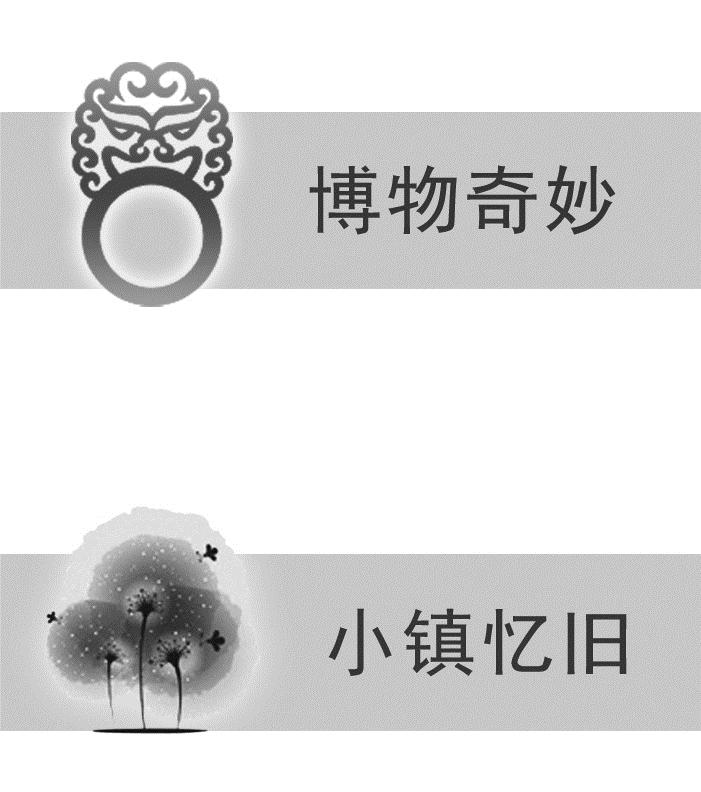他早就从落榜的阴影中走出来了,他谈笑风生,一副世界全在他掌控中的样子。
□刘剑波
信发在下海取蛤方面运气总是杠杠的。文蛤分布于滩涂极不均匀的,有的区域麇集成堆,有的地方却极为稀少,更气人的是,两者往往相隔几步远。信发就像是长了一双金睛火眼,能瞬间看透沙泥表层下文蛤的分布情况,每次都满载而归。而我永远是倒霉蛋,永远碰不到信发那样的好运气。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下海的场景。我看到一个文秀的少年——他原本白皙的面庞被海风吹得通红——躬着腰,孜孜矻矻地拖着铁刨,他的耳朵像警犬那样如临大敌般竖着,谛听着铁刨底下的动静,抓着文蛤叉的右手随时准备勾取被铁刨刨出来的文蛤。因为过于紧张,我的右手甚至痉挛起来。可是我耕耘的那方滩涂太贫瘠了,铁刨拖多远也不“发市”。实际上,铁刨犁开沙土的声音十分动听,仿佛是来自于遥远的梦境。后来我发现,这声音与裁缝的剪刀划开苏州丝绸的声音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多时候我被这声音迷住了。我甚至希望能永远这么拖着铁刨在广袤的滩涂上行走。我凌晨两点爬起来,赤脚步行二十华里,就是为了来听这迷人的声音,那也不错,问题是,这也太奢侈了吧。现在当我眺望很多年前的滩涂时,我看到我像个傻子,拖着铁刨在滩涂上走来走去,而不远处的信发却忙得不亦乐乎,他不停地将文蛤从铁刨底下勾出来,投篮似的扔进绑在扁担上的网兜里。有时扔偏了,文蛤就会砸到扁担上,发出“嘭”的一声。那时我又伤心又沮丧。我多希望信发把我喊到他的“领地”上有福同享啊,哪怕是做个暗示呢。其实我完全可以死皮赖脸地跑过去,分他的一杯羹。然而,强烈的自尊心阻止了我,而信发是那种闷头发财的人,你永远不要指望他会喊你过去。
不过,信发在另一方面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我是指考大学。信发虽然住在小镇东街头,很可能一度以“街上人”自居,但农村却是无法改变的现实。雄心万丈,抱负远大的信发一心想跳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门,而上大学显然是唯一的途径,我说过,信发是个勤学不倦的好青年,中学时代嗜书如命,到了忘我的地步。我印象最深的是,信发每次坐在灶门口烧锅,都会就着灶膛里的火苗看书,上茅缸也是手不释卷。信发单独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我每每午夜梦醒,从窗户隔着马路看过去,信发小房间的灯还亮着。恢复高考那年,信发志在必得,浑身散发着“舍我其谁”的气息。本来就有功底,考试前又上了补习班,信发信心爆棚。那年我十七岁,在高考的大军里也闪动着我怯懦的身影。那年,因为搬家,我与信发短暂分开了。短暂,是因为两年后我家又搬回到小镇上了。那年高考是在初秋,等到分数出来,已经是深秋了。我接到体检的通知后,以睥睨天下的神气骑车朝县城驰去。途经小镇一带,恰与信发相遇。其时信发正在田间挑粪,他当然也在等待体检的通知。以他自命不凡的秉性,他毫不怀疑通知他体检的信件正行走在路上,不日将交到他手中。所以他在等待中耐心做着农活,他也许会想,我就要告别农活了,我以后再无机会亲近庄稼了,他以依依不舍的心情做着农活。他做农活的农田傍着马路,所以他一眼就发现了我。他问我去哪儿。我却反问他有否收到体检通知。他落寞地摇摇头。那时我已估猜信发落榜了,我以小人得志的神情洋洋自得地告诉他,去掘港体检。听我这样说,信发脸色立马变得苍白。后来我发现,失恋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脸色。我用冠冕堂皇的话安慰他,明年再考嘛,大学的门是永远朝着年轻人敞开的。我骑出很远,回头看了一眼,信发还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儿。
信发是那种除非你消灭他的肉体,而在精神上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人。我在读书期间——我读的师范设于县城——信发时常来看我。他早就从落榜的阴影中走出来了,他谈笑风生,一副世界全在他掌控中的样子。他告诉我,他终于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在家里开了个电器维修铺。信发是有才的,维修技术完全是无师自通。终日蜷缩于一堆待维修的电器中,边谋生边复习,来年再战。不幸的是,来年他又重蹈覆辙,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但信发并不气馁,又开始第三次备考。当时我就读的师范,其实是培养中小学教师的速成班,我们只读了一年半,就分到学校实习了。说是实习,其实是独当一面,正儿八经地做起教师来。命运注定要将我和信发捆绑在一起,就在我分到小镇中学时,信发恰巧也在该校代课,教史地课。上史地课的好处是不必批改作业,信发上完课就一头扑进高考复习资料里。那些高考复习资料,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了,早已耳熟能详,但信发还是像当年下海那样,将专注的目光当成铁刨,在那些“高考必读”的“滩涂”上不倦地耕作。信发是被当编外教师对待的,所以他被学校安排在体育室办公。体育室是堆放体育器材的地方,体育教师纪康安也在里面办公,信发被挤在角落里。但信发相信,他能在角落里起飞。小镇中学偏僻闭塞,年轻教师的精神生活似乎只有依赖于谈恋爱一途了,所以当我跟一位姓薛的女教师欲修秦晋之好,人们并不觉得奇怪。我们白天要忙于教书育人,无暇沐浴爱河,只好留在晚上了,这就好比把最好吃的菜留到最后。我发现,在白昼沐浴爱河与在星光下沐浴爱河,绝对是两种感觉。每天晚上谈完恋爱,已经是夜半更深了,而信发还在体育室复习,他伏案的背影在我看来多么悲壮。这让刚从温柔乡出来的我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后来我想,那种负罪感是对过早谈恋爱而挥霍时间的觉醒和愧疚,而让我绝望的是,我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再后来,我又觉得那种负罪感是上苍对我的惩罚,爱情是罪愆的同义词,过早盲目地触摸它,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而那种负罪感其实是对你发出的信号。信发连考五年,均以几分之差与大学校门失之交臂。该有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经受住这样的失败。后来信发考上了如东电大,这多少安慰了他,不管怎么说,“电大”也算是大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