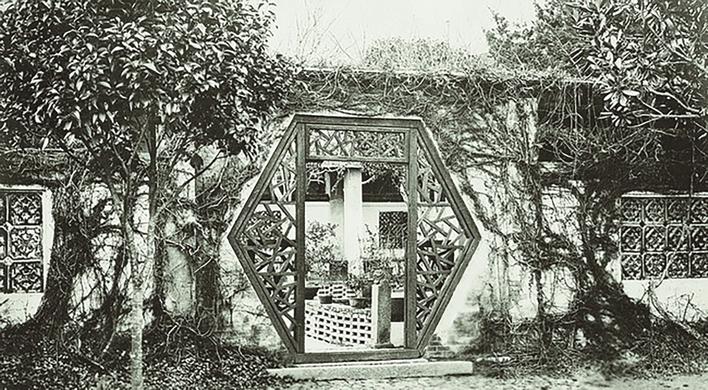□朱江
张謇与上海的关系,以1895年为界,之前是观察和学习阶段,之后则是张謇把上海视作自己施展抱负的舞台。如果说南通是其实业基地,并因实业的发展带动教育和公益慈善事业的进步,进而促进南通的早期现代化。那么南通的进步和发展,给了张謇足够的自信和资历,使他得以在上海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展示。
青少年时代的张謇对上海的认知,与其父亲张彭年有密切的关系。张彭年身处海门常乐,当年这个地方既不滨江也不临海,更不是因盐而兴的集镇,其实很闭塞。但是张彭年是个头脑灵活善于进取的商人,他的见识远超乡人,为家庭带来大量的外部信息,特别是来自上海的新鲜故事。
张謇的《述训》里提及,张彭年先是有瓦屋5间、草屋3间,后来又陆续添建了房屋。张彭年初有田20余亩,后来有所增加,还兼营瓷器,算是比较富裕。张彭年还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先君子营柳西草堂二楹,有书八椟,题以‘自随’”,张彭年较早的时候就有8木柜的书籍。张彭年具体有哪些书不得而知,但从他晚年喜欢研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看,张彭年务实而钻研,张謇日后在给儿子张孝若的信里说:“儿宜自勉于学,将来仍当致力于农,此是吾家世业”,不能不说受张彭年的影响。
1848—1850年间,连年灾害,张彭年借钱外出做生意,“附舟至上海,转商于宁波”,从海门坐上小船到上海,再赶往宁波。去宁波,很有可能是采购瓷器,因为宁波是中国的瓷业中心之一。这里的核心,在于张彭年需要在上海中转,那时的上海已经于1843年开埠,正逐渐向中国最大的城市发展中,外国商品和技术纷纷涌入,中西文化在此交融和碰撞。上海的繁华对于久居乡间的张彭年必然带来心灵的冲击,望子成龙的他也一定会跟张謇讲述所闻所见。张彭年是经常性地来到上海,他娶了金夫人后,曾“岁半外出,一切经纪皆吾母手自厘绪”,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外经营,家里的事都是由张謇的母亲金夫人打理。1876年3月14日,张謇曾在吴淞搭乘家中购买碗的船回海门,由此可见张彭年的瓷器生意达到了一定规模,而且经营稳定,已经不需要自己直接去上海接运。
书报也是张謇与上海间接接触的媒介,《申报》是一个例证。《申报》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1949年5月27日停刊,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申报》是张謇了解时事,掌握新知的来源。1895年前的张謇日记,至少有7处阅读《申报》的记录,其中3次是在海门,最早是在1884年5月16日,张謇在海门通过《申报》,“知吾军有调防奉天之讯”,此处“吾军”指吴长庆所率的淮军。能在海门乡间读到《申报》,张謇显然有稳定的获取渠道,凭张謇的家庭条件和张彭年的开明程度,长期订阅也有可能。《申报》扎根上海,必然把沪上新闻不断带给张謇,长年累月阅读下来,上海已然是个熟悉的城市了。
百闻不如一见,创办大生纱厂之前,张謇有很多机会来到上海。上海的经历,张謇在日记里一般只是记载生活起居和人际往来情况,几乎没有对上海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发表看法。事实上,繁华的上海滩对于身处偏僻乡村的张謇,视觉和心理冲击力不会小。这种冲击不仅仅影响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同样也影响东瀛人士。1867年2月19日,日本的涩泽荣一等人乘坐的“阿尔菲”号靠岸上海,上海街道上煤气灯和电线杆让涩泽荣一的内心感到震撼。1895年张謇筹办大生纱厂开始,始终把上海作为其发展南通各项事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主要来源地,绝不是心血来潮。
张謇不仅看到上海生机勃勃的一面,认为“上海为全国商业中枢”,也体察到丑陋黑暗的一面。1878年2月20日,张謇从海门坐船到上海,当晚住在永安街太古昌洋行,季瀛洲邀请看戏。第二天,张謇上街购买扇袋、手巾、笺纸等物品。季瀛洲在兆荣里置酒请客,之后泾县胡媺斋相邀至朱雪卿、王素娥词史处。张謇目睹湖北涂某、湖南周某、陈某等人花天酒地,一夜用掉番钱70余枚,感慨“贫家终岁作苦,所得讵有此耶”。1920年秋,张謇倡导设立的淮海实业银行开设上海分行,张謇拟写了对员工的训词,他提醒员工“沪之地,人聚、财聚而恶聚之海也”,劝勉大家要忠于职守,遵守规则,勤奋工作。“人聚、财聚而恶聚之海”这句话,反映了张謇对当时上海的认知。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