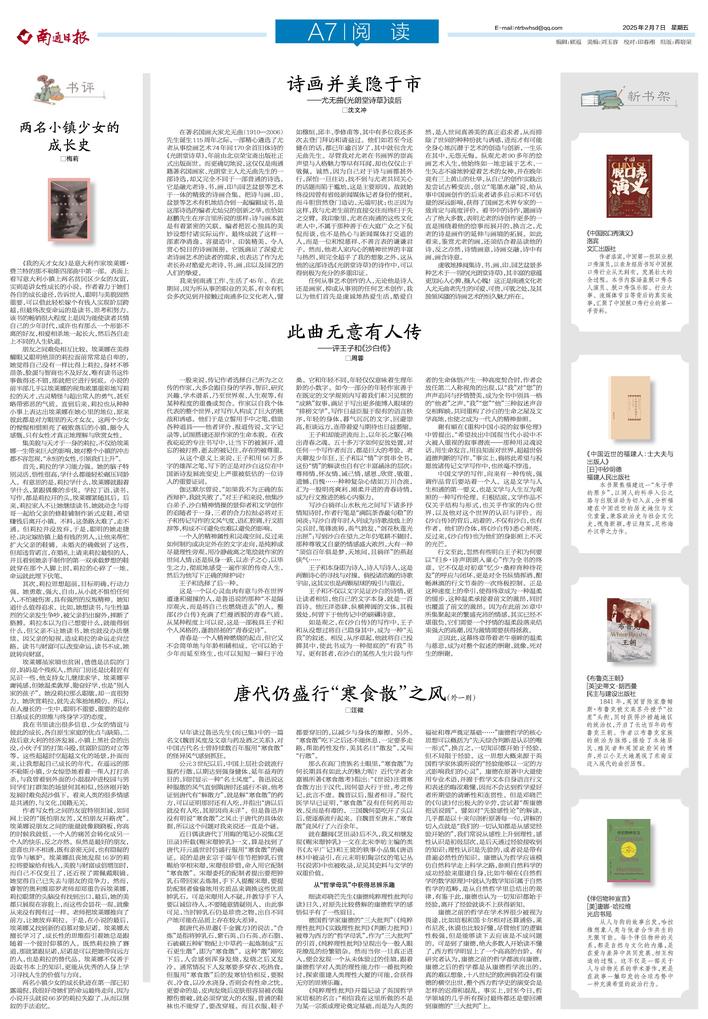□汪微
早年读过鲁迅先生《而已集》中的一篇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中国古代名士曾持续数百年服用“寒食散”的怪异风气感到抓狂。
公元3世纪以后,中国上层社会就流行服药行散,以期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显示一种“名士风度”。鲁迅说这种服散的风气直到隋唐时还盛行不衰,他考证到唐代有“解散方”,就是解“寒食散”的药方,可以证明那时还有人吃,并指出“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但是鲁迅并没有明说“寒食散”之风止于唐代的具体依据,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一直是个谜。
近日偶读唐代丁用晦的笔记小说集《芝田录》所载《赐宋璟钟乳》一文,算是找到了唐代开元盛世时仍盛行服用“寒食散”的确证。说的是唐玄宗于端午佳节把钟乳石赏赐给宰相宋璟,宋璟很珍惜,命人用它配制“寒食散”。宋璟委托的配制者提出要把钟乳石带回家去炼制,手下人提醒宋璟,要提防配制者偷偷地用劣质品来调换这些优质钟乳石。可是宋璟用人不疑,并教导手下人要以诚信待人,不要随意猜疑别人。由此事可见,当时钟乳石仍是珍贵之物,出自不同产地可能在品质上存在较大差异。
据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的说法,“合炼”是指将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硫磺五种矿物配上中草药一起炼制成“五石更生散”,即为“寒食散”。这种“散”刚吃下后,人会感到浑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通常情况下人发寒要多穿衣、吃热食,但服用“寒食散”后的发寒恰恰相反,要脱衣、冷食,以冷水浇身,否则会有性命之忧。更要命的是,皮肉发烧后皮肤很容易被衣服擦伤磨破,就必须穿宽大的衣服,普通的鞋袜也不能穿了,要改穿屐。而且衣服、鞋子都要穿旧的,以减少与身体的摩擦。另外,“寒食散”吃下之后还不能休息,一定要多走路,帮助药性发作,美其名曰“散发”,又叫“行散”。
那么在高门贵族名士眼里,“寒食散”为何长期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呢?近代学者余嘉锡所著《寒食散考》指出:“《世说》注谓寒食散方出于汉代,因何晏大行于世,考之传记,此言不虚。魏晋以后,服者相寻。”现代医学早已证明,“寒食散”没有任何药用功效,反而是有毒的。三国魏何晏吃开了头以后,便逐渐流行起来。自魏晋至唐末,“寒食散”竟风行了六百余年。
就在翻阅《芝田录》后不久,我又相继发现《赐宋璟钟乳》一文在北宋李昉主编的类书《太平广记》和王谠的轶事小品集《唐语林》中被录引,在元末明初陶宗仪的笔记丛书《说郛》中也被收录,足见其史料与文学的双重价值。
从“哲学母乳”中获得思辨乐趣
细读邓晓芒先生《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日久,对原先比较费解的康德哲学的感悟似乎有了一些眉目。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被尊为西方的“哲学母乳”,作为“三大批判”的引首,《纯粹理性批判》呈现出令一般人眼花缭乱的纷繁错杂。然而当你一旦真正进入,便会发现一个从未体验过的佳境,跟着康德哲学对人类的理性能力作一番批判检讨,探索重建人类理性大厦的可能,会获得无穷的思辨乐趣。
《纯粹理性批判》开篇记录了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相信我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奠定基础……”康德哲学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先天综合判断是认识的唯一形式”,换言之,一切知识都开始于经验,但不局限于经验。这一思想大概来源于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的“经验能够以一定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心灵”。康德在原著中大量使用专业术语,并囿于哲学文本自身语言行文和表述的晦涩难懂,因而不会达到哲学爱好者所期望的清晰性和连贯性。但是邓晓芒的《句读》付出极大的辛劳,尝试着“帮康德把话说圆”。譬如对“先验感性论”的解读,几乎都是以十来句剖析原著每一句,讲解的切入点就是“我们的一切认知都是从感觉经验开始的”,我们常说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感性认识是初级层次,是后天通过经验接收到的知识;理性认识是先验的,或者说是带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康德认为哲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走上科学之路,参照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来重建自身,比如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就认为数学知识属于自然哲学的范畴,是从自然哲学里总结出的规律,有鉴于此,康德也认为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离开了经验就谈不上获得新知。
康德之前的哲学在学术界很少被视为畏途,比如培根和笛卡尔相对还算通俗,莱布尼茨、休谟也比较好懂,尽管他们的逻辑性极强,但是能够读下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到了康德,绝大多数人开始读不懂了,西方哲学明显上了一个高高的台阶。有研究者认为,康德之前的哲学都流向康德,康德之后的哲学都是从康德哲学流出的。真的难以想象,十八世纪的欧洲倘若没有康德的横空出世,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演变会是怎样的迟滞和混乱。事实上,时至今日,哲学领域的几乎所有探讨最终都还是要回溯到康德的“三大批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