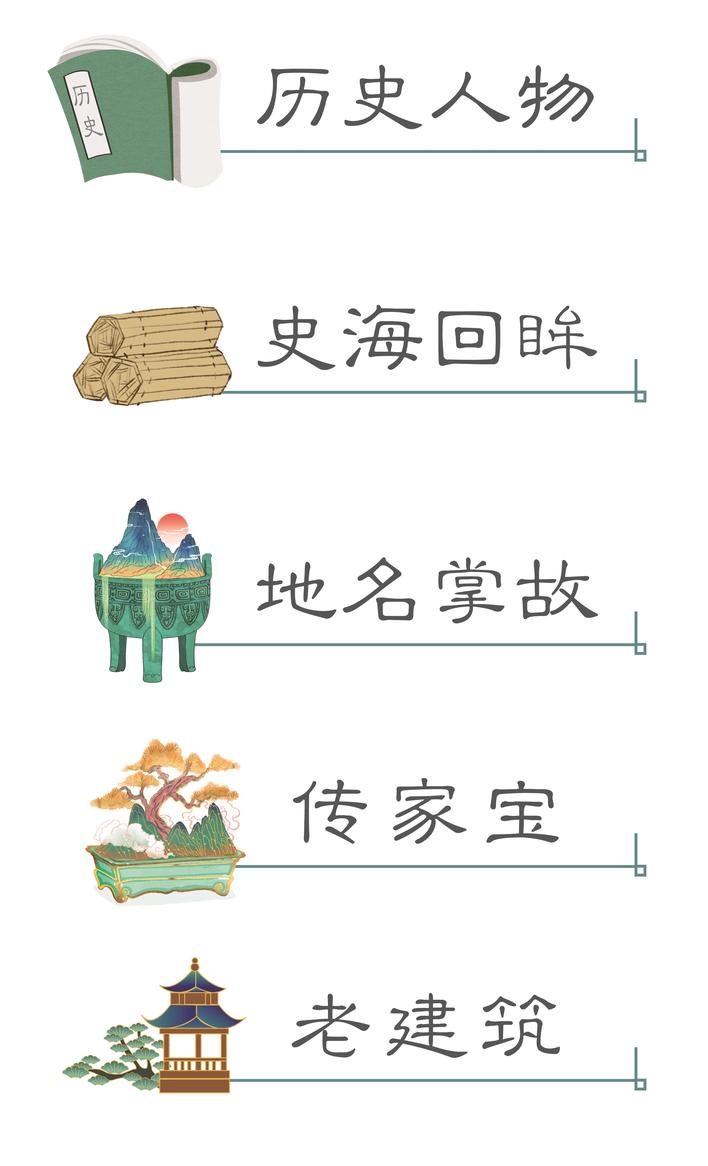□陈日铭
头总桥何缘而来?这要从“总”说起。“总”的名字来源于烧盐。烧盐的燃料是苇草,自古以来,如东沿海广阔的荒荡草田就是烧盐的燃料库。官府为了有序配置盐业用草,就将沿海荡田划分成和海岸线大体垂直的若干条块,宽的大约在一里左右,栟茶、丰利沿海民间有“三总合二里”的说法。官府把这些荡地出租给灶户烧盐取柴用,这样就把若干份长条形的荡田叫成若干“总”。“头总”即第一总。头总有一座跨河大木桥,因而叫“头总桥”。
头总桥范围为原范公堤南,今外农刘埠村三十五组、二十四组,它算不上镇,只能称为一条街。这条街呈东西方向,大约一里多长。呈南北方向的界港河将头总桥一分为二;一座大木桥架在河上,将两处连为一体。当时范公堤外盐民煮的盐经盐包场包装,由界港水路运到头总桥,然后一部分再由旱路运到各地。这里一度成为水陆运输的中转站。运往环港部队的物资也要经过头总桥水路。
1947年土改复查后,农民生活改善,一些头脑灵活的人看准头总桥的地理优势,在这里开起了小店;丰利、海安角斜、李堡等地的人也来此经商,开办小杂货店、粮行、理发店、缝纫店、鞋店、饮食店等。鼎盛时,桥东桥西有商店20多家。其中八鲜行3家,食品店、酒店4家,理发店4家,豆腐坊3家,肉店4家,杂货店3家。1949年后,政府在这里办起了供销社,兼收棉花,代收公粮。除此还有小糖摊、手提糖烟篮子叫卖的。一些草台戏班子、小马戏团也不定期到这里演出。
东街的供销社,东西一排房,社内各种商品都有。环农乡、环渔乡、杨家畈等地的人都到这里来购买所需物品。1958年,我读小学五年级。一天,我来到头总桥供销社买钢笔。我问营业员叔叔:“柜台里的花纹杆钢笔多少钱一支?”他说:“2元8角。”我身上只有2元6角。这位营业员主动为我垫付了2角。我接过钢笔,连声道谢!我打听到这位营业员叫严德艮。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东街头的电影场让我记忆犹新。这个电影场不是一个专门的电影场,而是借用张学家的场。这个场能容纳百人看电影。每当放电影时,我和伙伴们不顾路远,总要赶过来。电影场的小摊上卖糖果、瓜子和水果,偶尔我也买一点和伙伴们一起分享。如果我这次买了,下次他们就买。
东街上有一个缝纫店,师傅姓严,他戴着眼镜,脖子上套着皮尺。顾客来做衣服,可以在店里选布,也可以用来料加工。不管怎样,严师傅总是热情接待,顾客们对他的评价很高。西街上的缝纫店,两位师傅分别是洪吉祥和洪友山。还有卫生室里的朱家庆医生,他医德良好,热情服务,受人称赞。
东街上还有我的许多同学。徐维俊初中毕业后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单维新的父亲是锡匠,他跟着父亲学习技术。沈发如比我大两岁,他是一个勤奋学习的人。高中毕业后参加了教育工作,几年后被转为公办教师,后当上乡成人学校校长。他退休10多年了,正常参加老干部活动,还和老伴一起种地。徐永谦的命运不好,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如皋中学,可不幸患上类风湿关节炎,抱病数十年,今仍与疾病进行着斗争。
西街许福田开的八鲜行,为三行之最,每天都有交易。渔民们挑来文蛤、海鱼、海虾、海蜇、梭子蟹等,任人购买。那时的买卖与现在不同,渔民们到八鲜行卖海鲜都得由司秤员定价,说多少就多少,卖海鲜的人不可要高价,买海鲜的人也不能讨价还价。那位司秤员姓王,兄弟排行第二,人们习惯叫他王二,其实他的名字叫王长山。王长山每称一次秤,高声喊“哎,再记啊,×××红虾2元”,或“再记啊,×××黄鱼3元”,记账员沙可泉随声应答,他把王长山报的账一一记下。渔民卖完了海鲜,就到沙可泉处结账,扣除手续费,其余的归渔民所得。春夏之交买卖海鲜的人更多,从老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八鲜行的各种声音。东西三个八鲜行的声音和街上行人的声音交汇在一起,让小街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
西街徐福如脆饼店是我经常光临的地方。徐师傅加工的脆饼都是手工制作,黄灿灿的脆饼上沾满了芝麻,吃一口香酥可口。那时缺钱,每次我至多买1斤。与徐师傅脆饼店挨着的徐福庆馒头店,蒸的老酵馒头,口味特别好,每个馒头只卖2分钱,很多人都喜欢买。
西街上还有陈正新理发店,他笑脸迎客,热情服务,礼貌送客。理一次发只收5分钱。还有一个理发店,师傅叫钱乃贵,理发技术也很好。
头总桥还有一个特色市场——牛集市,行业术语叫“打旗”,农闲为每月一集,农忙暂停。牛集市这一天,在集市插上一面红旗或黄的小旗,将准备调换的牛拴在空场上,表示这是牛交易的地方。你若是对牛交易有意向,也可以到此地商谈。同时这里插旗(打旗)的牛主要是以牛易牛。这种牛集市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二十多年前,头总桥规模越来越小,八鲜行、粮行、供销社等先后撤销,各种商店相继退出。但它像一幅动静相融的美丽图画,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