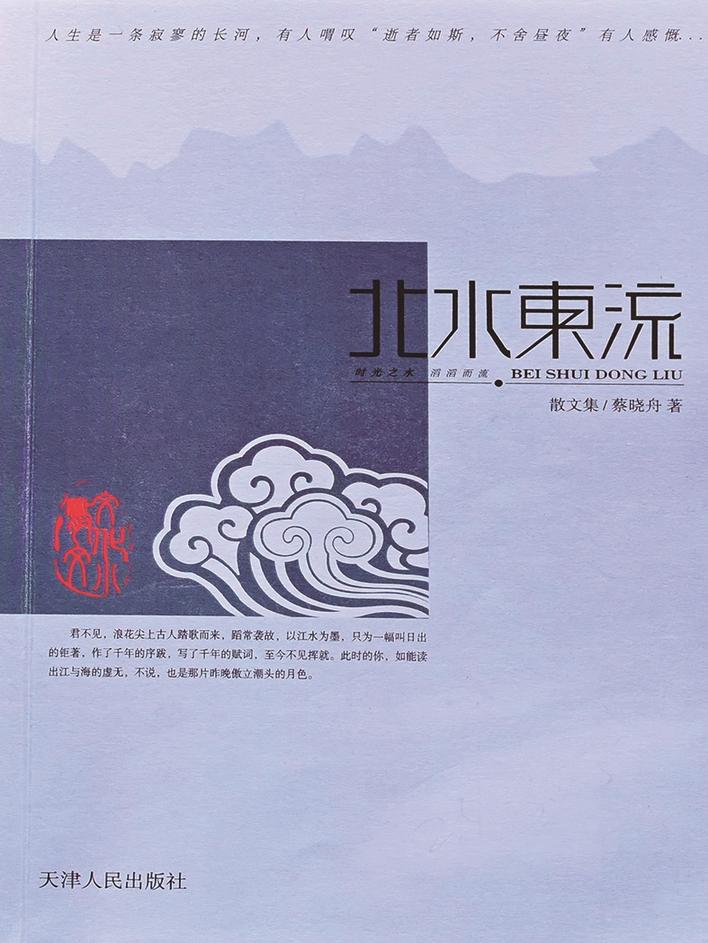□张华
在我眼里,晓舟是个诗人。贾平凹说:“诗,不养家,但养人。”这话更适合晓舟。
晓舟的第一身份是商人。去过他店里几次,小店两层,一层是他的“商业空间”和“物质空间”,摆满各种打印扫描装订设备。但他真正的用心之处不仅于此,也不甘于此。
他常以另一种身份出现二楼,这是他的“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在那里,他是一个摄影家。墙壁上挂满全国各地采风的作品,从历史长河的悠悠岁月,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每一帧画面都蕴含着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视角。在那里,他是一个作家。在那个维度,有明月高照,江水东流,有一群人的满地心思,一个人的独自狂欢,有夜半的钟声,远方的牧场。
晓舟爱文学,更爱生活。曾去过他筑于老家一隅的雅舍,屋内有字画,文气缭绕。屋前是一片精心雕琢的花园,不远处是条大河,多次出现在晓舟的作品中,见证了他品茗论道、举杯畅饮,见证了他文饭诗酒之间对文学的挚爱。
晓舟有诗性,更有才情。读过他的两本诗集《风吹芦荻》《心事》,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传达出对人生、自然和社会的思考和感悟。后来,他又认真写起了散文。他以诗人特有的观照方式和表达方式,巧妙地将诗歌的韵律、节奏和意象融入散文中,表达幽远的意境与细腻的情感,使散文既有诗歌的韵味和美感,又能融入深刻的哲理和启示。
他在《北水东流》中这样写道:“在潮音中完成原始积累的大小浅滩,每一粒沙子都是一个坚强的回归者,它们有终结流浪生活的主观愿望,有皈依田园的虔诚。江水沙土、相互依存。水滋润生命、土承载生命,它们始终因肩负人类生存道义而默契配合。一粒沙就是一滴水的内心:温热微凉,宁静躁动,清冽雄浑。沙,以静制动,或沉淀或远行但绝不玩消失。在潮音萦绕的生命群落,沙以细微之躯堆积了文明厚度,也为我们留下了披沙沥金的沙地文化。”
这种超现实主义的工笔叙事,以生动密集的意象,让生活之源、历史之源、文化之源、艺术之源、美学之源、哲学之源,散发出浓浓的诗性。晓舟的散文恰是诗歌的延伸和衍化,这是一种“诗性散文”。
再如《撑船篙子》:“少时,家有祖传木筷筒一只,上有麦豆图案交织成的繁写‘丰’字,寓意‘丰盛、足食’。却因年久失修几近散架,后经我土法修缮,才让这个居住在筷筒上的‘丰’字挽留下来。因素怀美好向往,这个伴随多年的‘丰’字,至今仍是我敬畏的汉字图腾。”
当今世界,喧哗浮躁,少有人能像晓舟这样,以极大的耐心打捞流年碎影,以古典的情怀追寻遥远的集体记忆。
再看《乡村之夜》:“头顶弯月如弓,一些浩瀚之想仿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倘若,身体也是一张弓,那思想就是弓上的弦,一声弓弦的惊响,就是内心灵魂的呼唤。物质的箭簇和精神之箭具有出发点相同、目的地各异的特点。又假如,和谐共鸣的弓弦,已了无开张之弹性,那些挂在腰间的箭囊还作何用?”
可以看出,作者已从日常的、“此岸”的书写突围而出,看到无形之形,听到无声之声,进而关注思辨的、形而上的世界,使文本的话语空间和思想空间得到极大拓展。
日常生活,芸芸众生,在晓舟眼里,都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除了诗人,谁能有那种“目有繁星、沐光而行”的意趣?所谓好的文章,无非就是完成日常叙事向艺术叙事的形态提升而已。
精彩的文字,都是跨界、打通和融合的产物,晓舟就是一个例证。从他的作品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个留着长发、手举相机,洋溢着鲜明个性、捕捉着生活中微小烟火的晓舟。
有必要指出和强调的是,晓舟的故乡书写,应是他近年来“精神原乡”和“文学原乡”一种志度气象的回归。原因很简单,他生于斯长于斯,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自己情感的烙印。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城市化的加快,“故乡”正在远去,甚至消失。面对这一困境,晓舟的故乡书写既是怀念和眷恋,记录和保存,挑战和考验,更是探讨和反思。它提醒我们,在发展的冲突和变迁中,要给乡土情结和文化记忆留有一席之地。
由此,又想到基层写作的意义这个话题,答案在晓舟那里已呼之欲出。基层写作者才是这方水土真正的体验者、观察者和代言者。他们不喜欢宏大也做不到宏大,但离生活很近,离文学很近,擅长日常叙事和生活修辞,动态性、渗透性、共情性和普适性都很强。在“晓舟们”看来,生活与文学紧密相连,互为镜像。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基层写作者们的写作,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学生态。
窃以为,生活大于文学,文学高于生活,诗意的文学很重要,热气腾腾的生活、触手可及的快乐更重要。“我见众生皆草木,唯有见你是青山。”愿我们以文学的名义,在生活中遇见更多美好。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