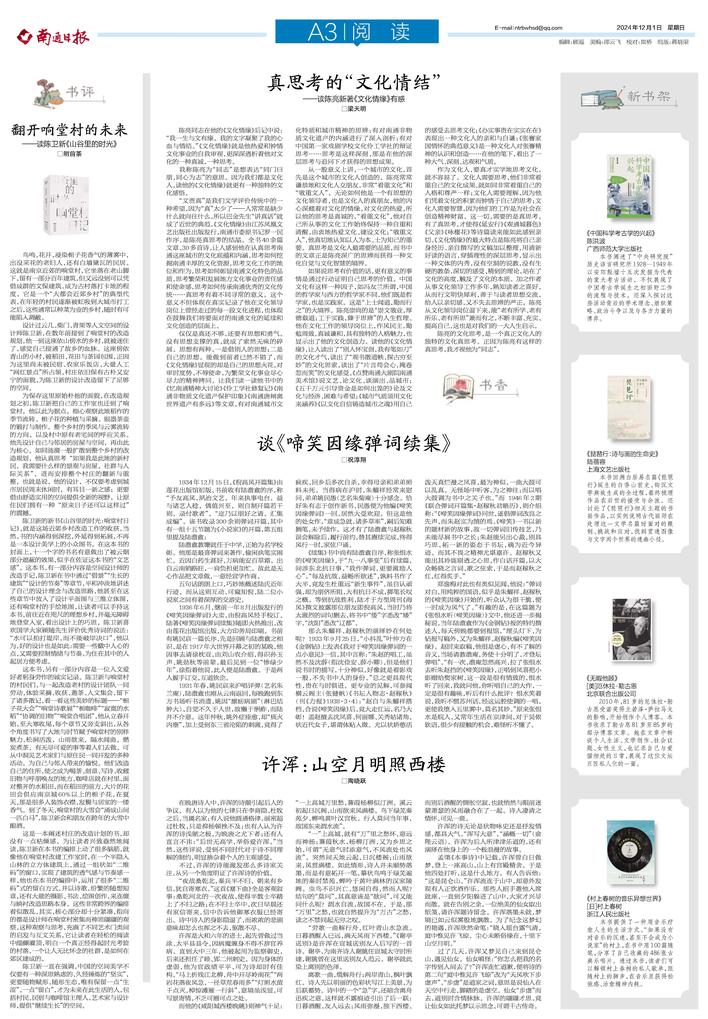□祝淳翔
1934年12月15日,《倪高风开篇集》由莲花出版馆初版,书前收有陆澹盦的序,称“予友高风,夙治文艺,年来执事电台,益与诸艺人稔,偶值兴至,则自制开篇若干则,录付歌者”,“迩乃以朋好之请,汇集成编”。该书收录300余则弹词开篇,其中有一组十五节题为《小说家》的开篇,第五组里提及陆澹盦:
陆澹盦教鞭就任于中学,正始为名学校彰。他那是最喜弹词来著作,偷闲执笔实闹忙。近因白药生涯好,万病能安百草霜。出自云南销路旺,一肩负担更加忙。故此是无心作品把文章做,一意经营学作商。
五句话朗朗上口,巧妙地概述陆氏近年行迹。而从这则互动,可窥知倪、陆二位小说家之间有着深厚的交游史。
1936年6月,继前一年8月出版发行的《啼笑因缘弹词》大卖,由倪高风经手校订、陆著《啼笑因缘弹词续集》随即火热推出,改由莲花出版馆出版,大方印务局印刷。书前有姚民哀一篇长序,先是回顾与陆澹盦之相识,是在1917年大世界开幕之初的某晚,他因事去请徐枕亚,由刘山农介绍,得识孙玉声、姚劲秋等前辈,最后见到一位“惨绿少年”,徐指着他说,此人便是陆澹盦。于是两人握手订交,互道钦企。
1931年春,姚民哀来沪唱评弹(艺名朱兰庵),陆澹盦也刚从云南返回,每晚跑到东方书场听书消遣,姚因“瘰疬病剧”(淋巴结肿大),自觉不久于人世,故懒于酬酢,而陆并不介意。这年仲秋,姚外症痊愈,却“痰火内壅”,加上受到东三省沦陷的刺激,竟得了疯疾,回乡后多次自杀,幸得母亲和弟弟照料未死。当得病在沪时,朱耀祥经常来慰问,弟弟姚民愚(艺名朱菊庵)十分感念。恰好朱有志于创作新书,民愚便为他编《啼笑因缘弹词》一回,居然大受欢迎。但这是他的处女作,“章成急就,诸多草率”,嗣后知难搁笔,未予续作。这才有了陆澹盦与赵稼秋误会解除后,履行前约,替其赓续完成,终得风行一时,家弦户诵。
《续集》书中尚有陆澹盦自序,称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于“九一八事变”后有续篇,间涉东北抗日事,“我作弹词,更要激励人心”,“每及抗敌,益畅所欲述”,孰料书作了大半,竟发生杜重远“新生事件”,虽自认顽强,却为朋侪所阻,大有抗日不成,掷笔长叹之概。等到抗战胜利,陆才于方型周刊《海风》撰文披露那位朋友即倪高风,当时乃将太激烈的词句删去,将书中“倭”字悉改“矮”字,“沈阳”悉改“辽都”。
那么朱耀祥、赵稼秋的演绎妙在何处呢?1933年9月25日,“小抖乱”叶仲方在《金钢钻》上发表《我对于啼笑因缘弹词的一点小意见》一信,其中言称:“朱赵的唱工,虽然不及沈薛(指沈俭安、薛小卿),但是他们说书时的描写,十分神似,好像就是看影戏一般,不失书中人的身份。”总之更具现代性,贵在与时俱进。更专业的见解,可参阅横云阁主(张健帆)《书坛人物志·赵稼秋》(刊《力报》1938·3·4):“赵自与朱耀祥搭档,合说《啼笑因缘》后,竟大走红运,名乃大彰!盖赵擅去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诸角,状近代女子,堪谓体贴入微。尤以状娇憨活泼天真烂漫之凤喜,最为神似,一曲大鼓可以乱真。无怪场中听客,为之神往;而以唱大鼓调为书中之关子也。”而 1946年2期《联合弹词开篇集·赵稼秋君略历》,则介绍称:“《啼笑因缘弹词》问世,遂倡弹词改良之先声,而朱赵实为鹄的焉。《啼笑》一书以新的题材新的故事,故一切弹词旧传技艺,乃未能尽展书中之长;朱赵能另出心裁,别具巧思,拓一新的姿态于书坛,确为近今异迹。而其不畏之精神尤堪嘉许。赵稼秋又能出其玲珑剔透之心思,作白话开篇,以大众畅晓之言词,歌之弦索,于是而赵稼秋之红,红得炙手。”
郑逸梅对此也有类似见闻,他说:“弹词对白,用纯粹的国语,似乎是朱耀祥、赵稼秋的《啼笑因缘》开始的,听众认为很干脆,便一时成为风气了。”有趣的是,在这篇题为《张恨水听〈啼笑因缘〉》文中,他还进一步揭秘说,当年陆澹盦作为《金钢钻》报的特约撰述人,每天傍晚都要到报馆,“埋头灯下,为钻报写稿外,又为朱耀祥、赵稼秋编《啼笑因缘》。赵时来取稿,他很是虚心,有不了解的音义,当场请教澹庵,务使十分明了,才登坛弹唱”。“有一次,澹庵忽然髙兴,拉了张恨水去听朱赵挡的《啼笑因缘》,正唱到凤喜把小影赠给樊家树,这一段是很有情致的,恨水听了回来,我就问他,你听唱自己的大作,一定是很有趣味,听后有什么批评?恨水笑着说,我听不惯苏州话,经这运腔使调的一唱,更使我堕入五里雾中,莫名其妙。”原来张恨水是皖人,又常年生活在京津间,对于吴侬软语,很少有接触的机会,难怪听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