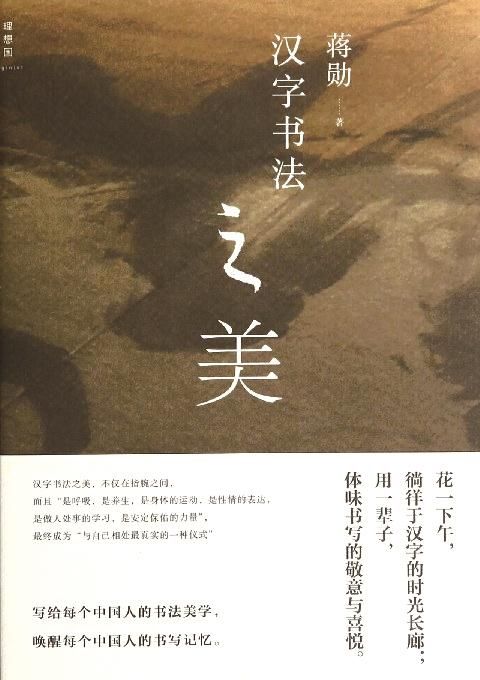□南西
习字之后,开始喜欢阅读书法类的书籍。新近读完蒋勋的《汉字书法之美》,收获颇多。
从序言中得知,蒋勋习字很早,三四岁就和兄弟姐妹,围坐同一张桌子练字了,由父亲的手握着他的手写。因此他对于书法的最初记忆,是与父亲的亲密身体接触。父亲一直不鼓励他写行写草,强调先打好唐楷基础。这对我很有启发。相对来说,楷书比行书草书更见功底。不好好临楷就直接写行写草,好似鸟之羽翼未满就着急起飞,总是飞不太远。
汉字书写,像一种修行。最初的九宫格描红,让蒋勋学到了“规矩”,领悟到汉字中蕴藏的中国文化。“规”是曲线,“矩”是直线;“规”是圆,“矩”是方。共鸣之处:最不敢写的是上、大、人,因为笔画简单,不能有一点苟且。最难写的是一,极致的素朴。
《汉字书法之美》正文共分为四章,分别从汉字演变、书法美学、感知教育、汉字与现代来展开叙述。于我来言,收获最多的是前面两章。
“汉字演变”章节里,不仅有包括仓颉造字、蒙恬造笔、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秦简、简册等等的书法知识输出,也有蒋勋对书法鉴赏的个人表达。
青铜铭文是书法史上所谓“大篆”的典范。石鼓文则是“大篆”转变为“小篆”的关键。“小篆”是李斯依据西周“大篆”创立的代表秦代宫廷正体文字的新书风。李斯撰写的《峄山碑》《泰山刻石》,都是“小篆”典范。面对秦简,才能真正有欣赏毛笔墨迹的快乐。后人在秦简上发现“快行”字样,就是现在的快递。书法的舞蹈性、音乐性,到了汉简隶书才完全彰显出来。唐代的狂草书法里就有很多与舞蹈互动的记录。
蒋勋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听觉文字与视觉文字引导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可能有极大的不同。他说在欧美读书或生活,常常会遇到“朗读”。用朗读做课程练习,为朋友朗读,为读者朗读,欧美大多数的文字都是建立在听觉的拼音基础上。汉字则是一个字一个单音,同音字多。同音字多,视觉上没有问题,比如“师”或“狮”,听觉上一样,但两个字写出来意思完全不一样,视觉上很容易分辨。但是朗读时就容易误解,只好在语言的白话里把“狮”后面加上一个没有意思的“子”,变成“狮子”。把另一个“师”前面加一个“老”,变成“老师”。“老师”或“狮子”,使视觉的单音文字在听觉上形成双音节,听觉上才有了辨识的可能。
在“书法美学”章节里,了解到建筑与书写之美的呼应。书法并不只是技巧,而是一种审美,包含线条的美、点捺之间的美、空白的美。西方通常追求竖直向上(比如哥特式尖拱教堂)的建筑审美,而东方则追求横向波折的审美。
在这章里,学到一个专有名词“波磔(zhé)”,用来形容隶书水平线条的飞扬律动,以及尾端笔势扬起出锋的美学。“波磔”指的是右下捺笔,这种笔画在隶书中有特殊的表现形式,称为“蚕头燕尾”。“波磔”如同中国建筑里的“飞檐”,建筑学者称为“凹曲屋面”。利用往上升起的斗拱,把屋宇尾端拉长而且起翘,如同鸟飞翔时张开的翅翼,形成东方建筑特有的飞檐美感。《诗经》里有“作庙翼翼”的形容。东方美学上对水平线移动的传统,在隶书“波磔”、建筑“飞檐”、戏剧“云手”和“跑圆场”都能找到共同的印证。原来,书法美学不一定只与绘画有关,在建筑或戏剧里也能找到相应的审美。学到这点之后,我想日后若我再去北京城欣赏那些飞檐翘角的皇家建筑,一定会收到更多的波磔之美。
此外,书法还是一个时代美学最集中的表现。唐代书法追求宏伟壮大,大多与政治历史息息相关,比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国事,也是家事。宋代的书法美学则追求素净空灵,如同水墨山水,更多是个人生活兴之所至的文稿诗词札记,平淡天真,比如宋代四大书家苏黄米蔡,他们被后世传颂的书法,不是他们的楷书,而是他们手书墨迹的诗稿。苏轼的《寒食帖》,与《兰亭序》《祭侄文稿》,此书法美学三件名作都是“文稿”,也就是未经修饰的“草稿”。提到草稿,“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也是一篇草稿,有写错的字涂黑的,有漏写的字补写在边上的。事实上,《兰亭序》确立了汉字书法“行草”美学的本质——追求原创当下的即兴之美,保留创作者最饱满也最不修饰、最不做作的原始情绪。
还谈到“文人画”,比如苏轼,他们文学意境高,书法好,因此以文人的书法笔墨入画,也就是以书法的优越性主导绘画,开创了“文人画”一格。比如“墨竹”,是用书法的撇捺笔法线条入画的。赵孟頫说他画奇石则是用书法上的“飞白”皴擦,画枯木是用古篆字的笔触,画墨竹需要了解精通写字的“永字八法”。所以人们常说的书画同源也就十分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