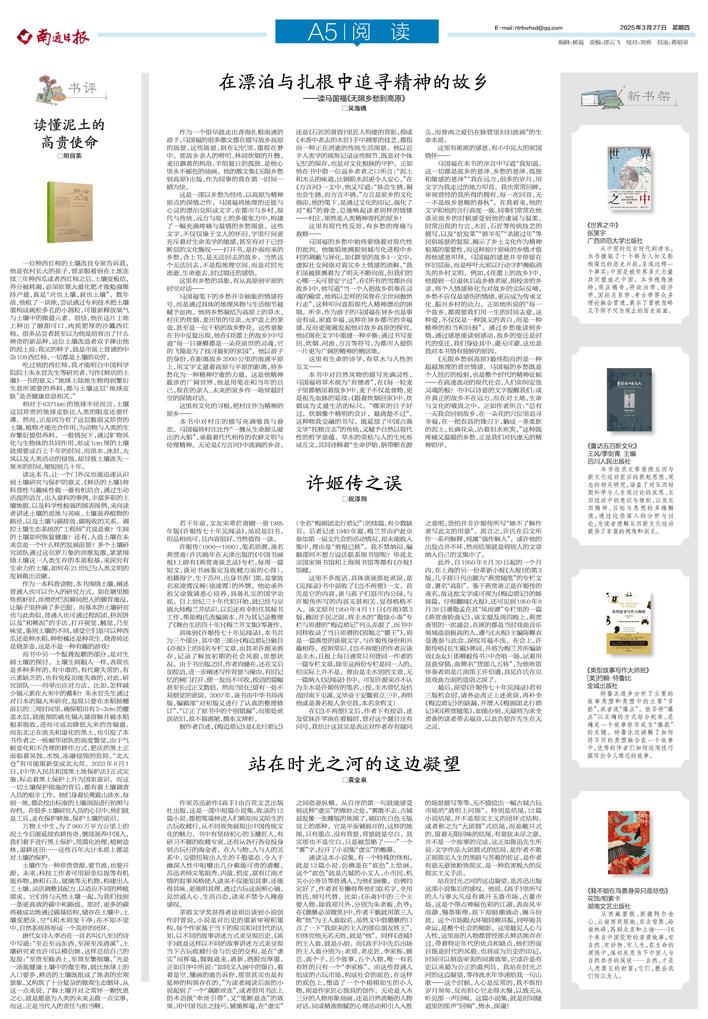□祝淳翔
若干年前,文友宋希於寄赠一册1985年版《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虽说是旧书,但品相尚可,且内容很好,当然值得一读。
许姬传(1900—1990),笔名思潜,斋名燕赏斋(许氏晚年在天津出版的《中国书画报》上辟有《燕赏斋谈艺录》专栏,每周一篇短文,谈论书画鉴定及收藏方面的心得)。祖籍海宁,生于苏州,出身书香门第,是掌故名家凌霄汉阁(徐凌霄)的外甥。他幼承外祖父徐致靖悉心培养,具备扎实的国学功底。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就已经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结识,以后还有幸担任其秘书工作,帮助梅氏改编剧本,并为其记录整理了《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文集》等著作。
具体到《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本书共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梅边琐记》辑自《亦报》上的同名专栏文章,由其弟许源来剪存,记录了解放初期的社会风貌、思想状况。由于书出版之时,作者尚健在,还在文后加按语,进一步阐述写作背景与缘由,有时记忆的闸门打开,便一发而不可收,按语的篇幅甚至长过正文数倍。然而当时已留有一处不易察觉的讹误。2007年,该书由中华书局再版,编辑部“对初版又进行了认真的整理修订”,“订正了原书中的个别错漏”,而那处讹误依旧,故不揣谫陋,撰本文辨析。
据作者自述,《梅边琐记》是《北行琐记》(全名“梅剧团北行琐记”)的续篇,有少数缺页。后者记述1949年夏,梅兰芳由沪赴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的活动情况,却未能收入集中,理由是“剪报已轶”。我不禁纳闷,编辑部何不想方设法联系图书馆呢?毕竟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都有《亦报》馆藏。
这里不多废话,具体谈谈那处讹误,是《见闻录》书中误收了《岂不两便》一文。首先是它的内容,谈与孩子们逛市内公园,与许姬传所写的内容无甚相关,显得格格不入。该文原刊1950年4月11日《亦报》第3版,概因手民之误,将圭木的“勤馀小奏”专栏与思潜的“梅边琐记”刊头弄混了,而书中同样收录了当日思潜的《别姬之“霸王”》,则是一篇典型的谈剧文字,与许姬传身份和兴趣相符。按照常识,《岂不两便》的作者应该是圭木,且报上每日通常只刊登同一作者的一篇专栏文章,除非这两份专栏是同一人的,但实际上并不是。理由是圭木别的文章,无一篇纳入《见闻录》书中。可知许源来亦不认为圭木是许姬传的笔名。(按,圭木曾忆及抗战时南下屯溪,又毕业于安徽省立三中,表明他或是著名报人余空我,本名余哲文)
在《岂不两便》文后,作者下有按语,述及堂妹许苹南在看稿时,曾对这个题目注有问号,我估计这其实是表达对作者存有疑问之意吧,恐怕并非许姬传所写“她不了解作者写此文的用意”。质言之,许氏在后文所作一系列解释,纯属“强作解人”。或许他的出发点并不坏,然而结果就是将别人的文章纳入自己的文集中了。
此外,自1950年8月20日起的一个月内,在上海的另一份革新小报《大报》的第3版,几乎排日刊出题为“燕赏随笔”的专栏文章,署名“高阳”。鉴于燕赏斋正是许姬传的斋名,故这批文字或可视为《梅边琐记》的姊妹篇。仔细翻阅《大报》,还可见到1950年8月28日潘勤孟在其“风雨谭”专栏里的一篇《燕赏斋聆曲记》,该文提及周四晚上,燕赏斋里的一次盛会,在座的都是当时戏曲音乐领域造诣极高的人,潘与《大报》主编陈蝶衣受邀参与此会,深叹耳福不浅。在会上,许姬传唱《长生殿》弹词,并将为梅兰芳所编新戏《龙女》(即柳毅传书)中合唱一场,试着用昆曲穿插,曲牌名“货郎儿五转”,为他吹笛伴奏者则是江南笛王许伯遒,具见许氏在京昆戏曲方面的造诣之深了。
最后,深望《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若有三版机会时,请务必改正上述讹误,再补全《梅边琐记》的缺漏,并增入《梅剧团北行琐记》和《燕赏随笔》,如能办到,无疑将为求全责备的读者带去福音,以此告慰许先生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