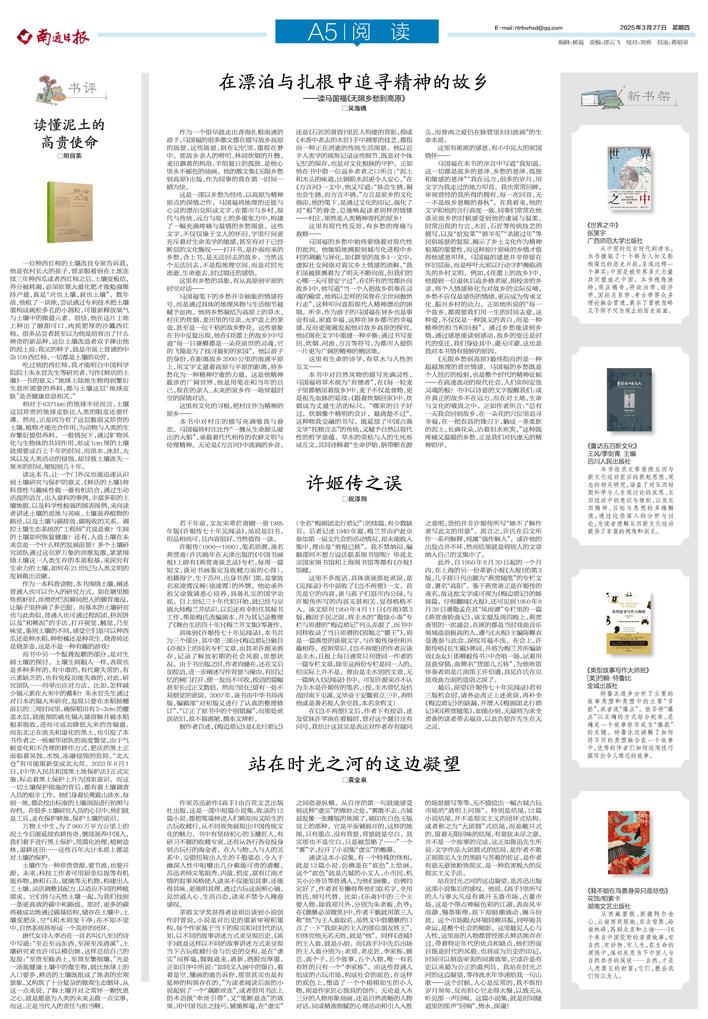□吴海嫣
作为一个很早就走出青海扎根南通的游子,马国福的很多散文都在描写故乡高原的场景,这些场景,刻在记忆里,重现在梦中。那故乡亲人的唠叨、林间炊烟的升腾、麦田飘黄的热浪、羊倌夏日的孤独,是他心里永不褪色的油画。他的散文集《无限乡愁到高原》出版,作为同事的我在第一时间一睹为快。
这是一部以乡愁为经纬、以高原为精神原点的深情之作。马国福将地理的迁徙与心灵的漂泊交织成文字,在都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远方与故土的多重张力中,构建了一幅充满疼痛与温情的乡愁图景。这些文字,不仅仅缘于文人的怀旧,字里行间更充斥着对生命美学的敏感,甚至有对于已经断层的文化慨叹——打开书,是扑面而来的乡愁,合上书,是无法回去的故乡。当然这个无法回去,不是指地理空间,而是对时光流逝、生命逝去、时过境迁的感悟。
这里有乡愁的具象,有从高原到平原的时空对话——
马国福笔下的乡愁并非抽象的情感符号,而是通过具体的地理风物与生活细节被赋予血肉。他将乡愁凝结为高原上的草木、村庄的炊烟、麦田里的母亲,火炉盖上的茶壶,甚至是一包干枯的故乡野花。这些意象在书中反复出现,他在《花蕾上的故乡》中写道“每一只蝴蝶都是一朵花前世的灵魂,它的飞翔是为了找寻最初的家园”。他以游子的身份,在距离故乡2000公里的南通平原上,用文字丈量着高原与平原的距离,将乡愁化为一种精神疗愈的力量。这是他精神跋涉的广阔世界,他是用笔在和当年的自己、现在的亲人、未来的家乡作一场穿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这里有文化的寻根,把村庄作为精神的原乡——
本书中对村庄的描写充满敬畏与眷恋。马国福将村庄比作“一艘从生命源头驶出的大船”,承载着代代相传的农耕文明与伦理精神。无论是《方言河》中流淌的乡音,还是《石匠的黄昏》里匠人佝偻的背影,抑或《木香中老去的木匠》手中凋零的技艺,都指向一种正在消逝的传统生活图景。他以近乎人类学的视角记录这些细节,既是对个体记忆的保存,也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正如他在书中借一位返乡老者之口所言:“泥土和木头的味道,比钢筋水泥更令人安心。”在《方言河》一文中,他又写道:“铁会生锈,铜也会生锈,而方言不锈。”方言是家乡的文化烙印,他的笔下,是通过文化的印记,强化了对“根”的眷念,总能唤起读者别样的情愫——村庄,果然是人类精神寄托的原乡!
这里有现代性反思,有乡愁的疼痛与救赎——
马国福的乡愁中始终萦绕着对现代性的批判。他敏锐地捕捉到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凋敝与异化,如《群里的故乡》一文中,虚拟社交网络对真实乡土情感的消解。“我们虽被挟裹着为了明天不断向前,但我们的心哪一天可曾安宁过”,在《所有的雪都扑向故乡》中,他写道“当一个人把故乡供奉在灵魂的殿堂,他将以怎样的风骨在尘世间傲然行走”,这种叩问直指现代人精神漂泊的困境。所幸,作为游子的马国福在异乡也是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这种在异乡都市的幸福感,反而更能激发起他对故乡高原的探究,他试图在文字中重建一种平衡:通过书写麦田、炊烟、河流、方言等符号,为都市人提供一片更为广阔的精神的栖居地。
这里有生命的诗学,有草木与人性的互文——
本书中对自然风物的描写充满灵性。马国福将草木视为“有德者”,在《每一粒麦子里都栖居着故乡》中,麦子不仅是食物,更是祖先血脉的延续;《跟着炊烟回家》中,炊烟成为丈量生活的标尺,“哪家的日子好过,炊烟像个精明的会计,最清楚不过”。这种物我交融的书写,既延续了中国古典文学“托物言志”的传统,又赋予自然以现代性的哲学意蕴。草木的荣枯与人的生死形成互文,共同诠释着“生命伊始,脐带断在源头,而骨肉之爱仍在脉管里汩汩流淌”的生命本质。
这里有浓浓的感恩,有小中见大的家国情怀——
马国福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故乡的恩泽、乡愁的恩泽、孤独和敏感的恩泽”“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用文字为我走过的地方叩首。我也常常回眸,审视曾经的我所得的拥有,每一次回首,无一不是故乡恩赐的春秋”。在我看来,他的文字和他的言行高度一致,同事们常常在他谈论故乡的时候感受到他的虔诚与温柔。时常出现的方言、木匠、石匠等传统技艺的描写,以及“拾发菜”“剪羊毛”“杀猪过年”等民俗场景的复现,揭示了乡土文化作为精神根基的重要性,而这种原汁原味的乡情才值得他感恩叩拜。马国福的感恩并非停留在怀旧层面,而是呼吁大家以行动守护濒临消失的乡村文明。例如,《花蕾上的故乡》中,他提到一位退休后返乡修老屋、捐校舍的乡亲,将个人情感转化为对故乡的实际反哺,乡愁不应仅是感伤的情绪,更应成为传承文化、振兴乡村的动力。正如他所说的“每一个故乡,都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爱,这种爱,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表白,而是一种精神的担当和回报”。通过乡愁能读到乡情,通过感恩能读到感动,故乡的变迁是时代的变迁,我们身处其中,避无可避,这也是我对本书情有独钟的原因。
《无限乡愁到高原》最终指向的是一种超越地理的普世情感。马国福的乡愁既是个人经历的投射,也是整个时代的精神征候——在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人们如何安放灵魂的根?书中以诗意的文字提醒我们:或许真正的故乡不在远方,而在对土地、生命与文化的敬畏之中。正如作者所言:“总有一天我会回到故乡,在一朵花的穴位里追寻幸福,在一把农具的锋刃下,躺成一垄柔软的泥土,长满花朵,沾着泪水欢笑。”这种既疼痛又温暖的乡愁,正是我们对抗虚无的精神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