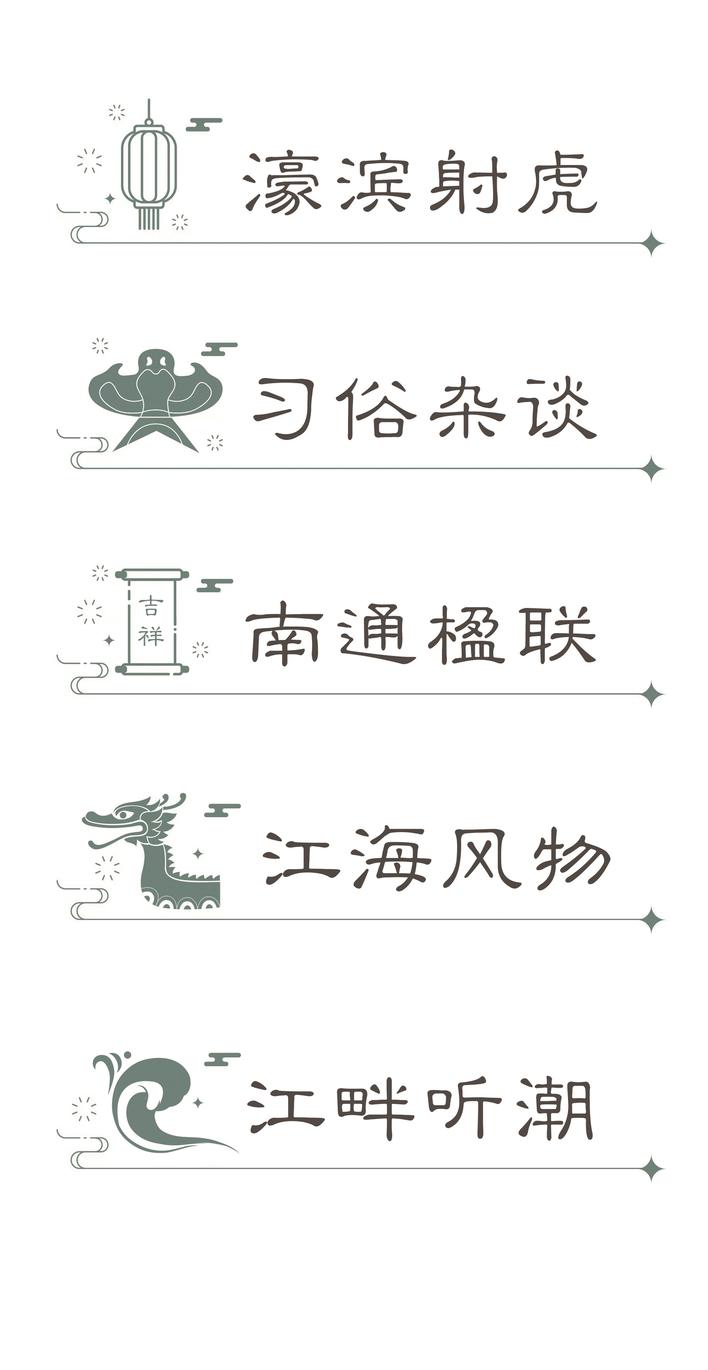□关立蓉
小时候,我常到祖母家玩,吸引我去的,是祖母家附近有一个木器铺子。
木器铺子建造在村里一条大河边,四周空旷,有一个金色的大铁门,用几领苇席围圈,上覆石棉瓦。我还记得很久以前的情景,被剖开的木板晾晒在河滩上,阳光下白花花一片,刺得眼睛疼痛。柳木、槐木、桐木……死命散发着香气。简易的工棚内,木匠师傅们做着新家具。一个年轻的工人背对着我,弓着黝黑油亮的脊背,用刨子刨一块木板,随着他的每一次用力,他背上、肋下、胳膊上的肌肉,像有一群动物来回滚动,无数的汗珠子折射出的明亮的光,甩在地上,干裂的地上,有潮湿的印记。那情景曾深深震撼着我,我有点畏惧地站在一旁观看,在他们的呵斥声中不时挪动着位置,并伺机捡拾一两块被丢弃的小木块。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忘记了那些木头最后被做成了什么,只是惶恐它们被肢解又被拼接的过程,那样浓烈残酷的香气,曾怎样吹动着一个孩子的心。
我那时想,木头也是有生命的吧?它们被剖开。那些香味应该是它们释放疼痛的方式吧。怎样才能弄明白一棵树?木板、木条、刨花、锯末……剖开的木纹在桌面上唱歌,一弯雕刀,可以呈现喜鹊、牡丹、月亮……仿佛一个世界对另一世界的追逐。这儿是离疼痛最近的地方,许多东西都在创造疼痛,斧子、刨子、钉子、锤子……而树木本身抿紧了嘴唇,它不知道叫喊吗?
似乎没有见过丑陋的树,每一棵树都以自己遒劲的或柔软的枝条展示着魁伟或者婀娜。但见过让人别扭的家具,那些拼接的生硬线条,即使给它涂抹上厚厚一层桐油,仍然可以看见它的局促不安。木器铺的周围,是河水、成片的芦苇,葳蕤鲜活的草木,沿着芦苇荡走上很远,在它的下游有密密的树林,树林像绿色的巨龙朝远方伸展,看不到尽头,我想河水有多长,树林就有多长,它将一直伸展进邻近的村子。只有这样的树林里才能产生大树,如云的树冠,浓郁潮湿的氧气,有百鸟和野兔出没。木器铺子需要这些大树。
这样的情景已不复存在,现在,那条大河已经蜷缩成一条小河,河面上油腻的一层,泛着不清不白的光。那些古老的树林已经不复存在,木器铺也早已改变了模样,它的地盘扩大了,被一片贴着瓷砖的高墙包围起来,墙外面没有庄稼,也没有民居,原住的居民得到了木器厂的一笔钱,远远地搬离,八个轮子的大吨位卡车拉过来木材,还有化学试剂粘成的胶合板,混合着油漆浓郁的味道。
再次走进这座木器铺,它已更名为木器有限公司,它的设备已现代化,电锯、电钻、电刨子、车床……木匠们只需抓牢机器的把柄,钢铁的锋刃摩擦出的热和火花,木头,依然有种焦香气息。电锯嘶鸣,木条仿佛肋骨分崩离析。
我看到了我在年少时曾让我惶恐的那位师傅,他已很老了,头发花白,明显佝偻着腰,他套在一件衣服里,又空又大。他不必再卖力地刨木头,他手里拿着一把凿刀,在一根已经光溜的木头前有些迟疑,像手拿一把老旧的探照灯,照着躺在黑暗中的木头。过了一会儿,他丢掉凿刀,捡起了一小块硬杂木,比画,打量,然后咕哝着一句,一缕神秘的微笑,从他脸上木刻似的皱纹中泛起,也许,他想起可以肆意拨弄这些木器的沉静光辉的时代……
电锯又吼叫着,撕裂了这片刻的安静,笑容消失,他又埋头凝神于他的打磨。这些树木,以各种姿态在他心里撑起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