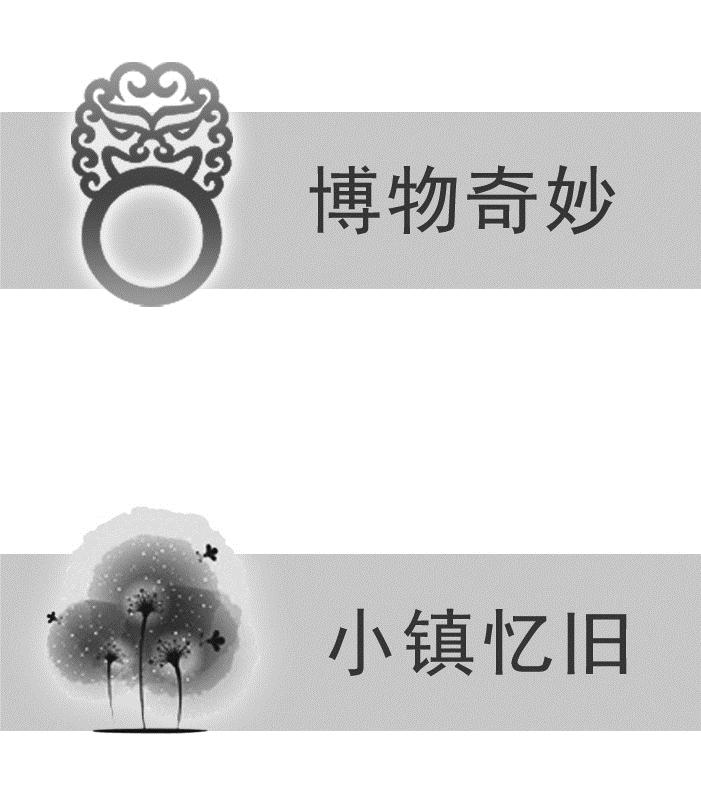民族文化大融合,本身就是相爱相杀的过程,强大的文化终究会改变影响弱小的文化。
□强雯
“山侵河处河镜倾,河侵山处山岭遶”,一米二高的山花碑,阴文,华丽中浸润伤情。云南大理苍山洱海的美与哀,在全碑楷书中显得正式而汹涌不绝。山花碑碑质为大理石,藏于大理市博物馆碑林,号称白族第一碑。
碑刻,镌刻在石头中的字词,没有一个字是白写的。一个侵字,让人思量其深意。
翻开历史卷宗,确实有深意。这与元末明初的各方政治、军事势力有关。
朱元璋虽然击败了大多数元朝参与势力,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设洪武元年,但云南一带在明初并未纳入版图。天高皇帝远,何况是开国皇帝,人家地方势力强大,不买账也说得过去。
不过云南一带坐地为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政治联盟。那时,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一带依然处于元梁王的据守控制之下,臣属蒙古“北元”政权,那梁王凭借边疆山高皇帝远和苦心经营云南百年的根基实力,自坐为大。当时云南的主要蒙元势力,有蒙古政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大理国王后裔——土酋段氏总管段明。梁王,以昆明为统治中心,大理段氏,控制着滇西一带,都听从北元指令。
这让朱元璋如鲠在喉。
“云南僻远,不宜烦兵”。明朝初期,朱元璋以招安为策。先后七次派出使臣前往滇地召谕梁王,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梁王一口回绝,并几次杀害明朝使臣。颜面尽失,也得咽下这口气。
直至国力休养生息了十余年,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决定以武力征讨:“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刺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招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
在云南曲靖的白石江战役中,血流成河,明朝军队所向披靡。后直逼昆明,将梁王的政权一锅端。明军继续南下,到达大理。洪武十五年(1382)闰二月,段氏后院大理被明军攻克,第十二世段氏总管段明束手就擒。
半年之后,云南江山易主,尽归明朝。为开发西南,巩固边防,明太祖下令,在云南省府昆明建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着手处理接收云南事宜——奉旨将蒙古梁王集团成员,梁王家眷、元蒙上层官员和大理段氏贵族头领全部押解北方,交由朝廷处置;清扫元朝残余势力和大理地方势力,就地遣散并安置数十万蒙古俘虏士兵;建立明朝新的政权机构;于军事要冲地区设置卫所,屯兵戍守。之后,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傅友德、蓝玉率部分征南大军班师回朝,留下沐英继续镇守云南。
成为大明王朝的一部分后,白族人自然要服从汉文化的管理。作为文化共融的时期。泱泱汉文化正在大肆拥抱、改变白族的文字、文学创作、文化理念,甚至官场条例。
最敏感的当是白族的文人。
山花碑是这个时期的孕育物,碑上共有10首山花体诗歌,排列整齐,看上去也十分利于朗诵,不过初读山花碑,大的美感很快被细读的艰涩所替代,有些词句简直是不通,后来才发现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写白语、读白音、解白义。白族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字。碑上刻的,就是这样的古白文。比如,“长寻细月白风清,不贪摘花红柳绿。用颜回道譃浮生,得尧天法度。”这还算是比较好理解的,是说,月白风清之日,不要贪爱繁花之美,用颜回的道术来理解虚浮的人生,就能得到像皇帝尧一样的盛世景象。
而有的句子能在汉语俗语中找到对应,但是个别的字词,却在字典中查找不到,比如“分数哽侔圡成金,时运车舛金成土,聚散佀浮云空花,实阿芣不无。”这句话的意思,在《金瓶梅》《三言二拍》《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都有提及,其表述是,时运来时土成金,时运走时金成土。悲欢离合一杯酒。聚散成败转头成空。
白族与汉族在文字上的姻缘,在山花碑上表达得其实比较甜蜜。民族文化大融合,本身就是相爱相杀的过程,强大的文化终究会改变影响弱小的文化。在山花碑上,读者甚至可以感觉到,我们不了解的白族,其实和我们一样,话语、情绪、人生体验,都是大同小异,虚无竟然是不分民族、地域存在的共同情感。这无形中拉近了我们对白族这个陌生民族的理解。诗句中隐晦的抗争,无力的抗争,也在唤起相似的历史记忆。比如汉文化历史上刘邦项羽争雄,霸王别姬,痛与虚无,大致无差。
苍山洱海是大理白族人的家园,苍山景色向来以雪、云、泉著称。经夏不消的苍山雪,无论是阳春三月,还是萧瑟冬季,苍山都显得娴静安然,冰清玉洁。洱海,在古代文献中曾称为叶榆泽、昆弥川、西洱河、西二河等,位于云南大理郊区,为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因为湖的形状酷似人耳,故名洱海。
如此美好的仙境,却不能自己当家做主,白族人微妙的内心隐隐作痛。山花碑固然是对苍山洱海的赞美与抒情,却是透出某种抵抗和不甘。
山河美景,万般美好。而碑文后部分却是人生虚无不可把握之叹,“天堂是荣华新鲜,漂散成地狱。”
先扬后哀的歌调,是一个人看尽繁华背后的虚无与悲凉,这种声调,在清代《桃花扇》中,是同样的迷离。“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在《红楼梦》中,哀凉更是一阵阵入髓,叹富贵命运、王孙权贵,最后皆“白白茫茫大地,好个干净”。
山花碑碑文的作者,刻写在碑末的诗句中,名叫杨黼,生于明代,大理下阳溪人,其先辈是大理国和元代的望族,《明史·隐逸传》中载有他的传记。幼时读书万卷,但一直生活在民间,有不少著述,山花碑是他用白族民族传统的诗歌形式,所写成的洱海风光的山水诗之一。明代著名白族文人李元阳还专门为其写过《存诚道人杨黼传》。
但要真正读懂这些诗,还需要读一读山花碑另面刻写的《圣元西山记》。这其实是碑石的正面。它披露了杨黼的身世:远祖杨连在大理国时“为王左右”,祖父杨智系元代云南平章大理路总管段功家臣员外,曾授元帅。后段功被梁王所害,杨智闻说亦赴死,其父杨保也是段氏元帅,明洪武十五年(1382)傅友德率军平滇时,自缢殉国。家族的不幸,江山易主,百感交集,集于一文。
美则美矣,然人事无常,唯花叶草被,代谢不辍,苍山永恒,洱海唯新。渺小的命运和无穷的山川互为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