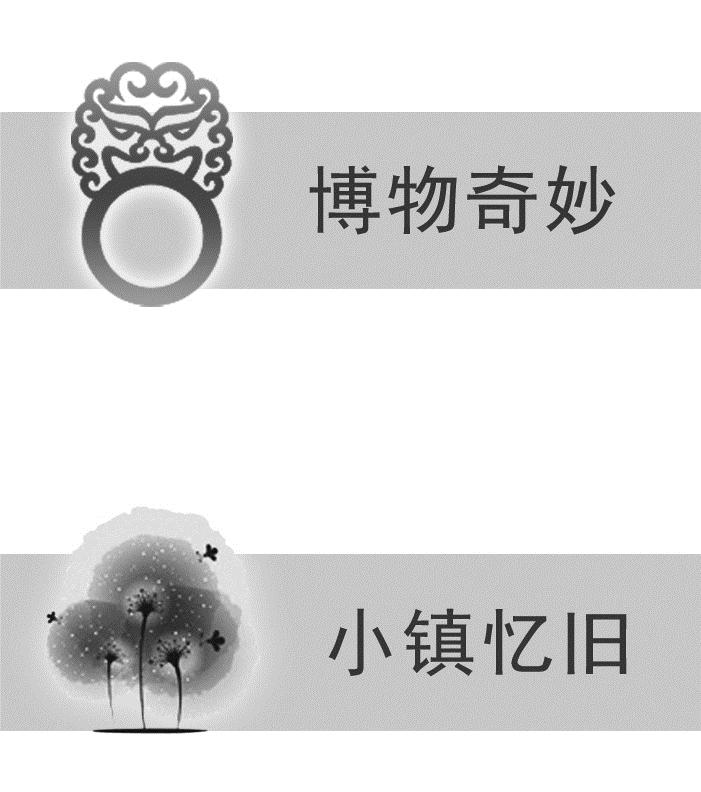□刘剑波
如果把矮壮的高粱比作粗犷的北方大汉,那么芦稷就是苗条的南方女子了,它的穗、叶、秆,处处透出秀气的水灵劲儿。
世界上有许多事物虽然名不见经传,却让你真实感到它的存在,感到它的温暖,感到它缄默、执著的力量,譬如小镇所盛产的芦稷。芦稷的形象介于江芦和高粱之间。江芦,小镇人称之为“gang芦”,我对它太熟悉了,我家东山头河边长满了这种植物,茂密而旷朗,我家的小猫每每上桌偷吃了美味佳馔,为避主人泄愤便躲避其间,让你无从寻觅,而在半夜梦回,我常听到它在夜风吹拂下发出林涛的低吼。小时候,我太迷恋芦稷了,就想,要是我家的江芦是芦稷那该多好啊。芦稷应该更像高粱,有些地方直接将之称为甜秆儿或甜高粱,但它与高粱毕竟有不同之处,如果把矮壮的高粱比作粗犷的北方大汉,那么芦稷就是苗条的南方女子了,它的穗、叶、秆,处处透出秀气的水灵劲儿。世上最甜的莫过于糖和蜜,但糖和蜜吃多了,自有腻的时候,而吃芦稷从不会使你有腻的感觉。每年的仲秋,暑热刚刚如八月十五的大潮退去,空气中还残留着些许躁人的汗腥味,蓦然间,在某一天清晨或某一天黄昏,芦稷便仿佛无数面紫红的旗帜,飘荡于小镇四周的沟边,摇曳于屋后,伫立于田坡,辉映于小河。无异于心灵感应一般,我们这些孩子看到镇东头河流那边的农人手持砍刀,钻进芦稷林,很快,便抱着一捆芦稷出来,这使得我们的贼心抑制不住地荡漾起来。
我记得我穿开裆裤的时候,就成了一名偷芦稷的老手。我偷芦稷不用跑远,陆善堂屋后的自留地里就长着大片的芦稷,而陆炳龙屋后自留地里的芦稷更多(小镇一带的人们,不仅不把偷芦稷的小孩视为贼,还要用种种称赞的语言奖励他,比如说,“那伢儿不简单,能拔得动芦稷哩”)。通常是,丢下晚饭碗,我就同某个小伙伴出发了,彳亍于牛羊咩咩的乡间小道,将各自身上精瘦的肋骨作风琴的键子弹着,唱起好多从广播里听来却不知其名曲子。月亮从东面一个墙豁口爬上来,如一根香蕉挂在一株老树的枝丫上。云彩也缓缓地从哪个角落里挪过来,因此月光不能朗照。我们选定了一家菜地上长着的茂密的芦稷林,便都钻了进去。芦稷林犹如几枚石子投进河面,荡起了一层涟漪后,复归于寂静。我们因为力小,通常不能连根拔起,而是将靠根处掰断。芦稷自有它的脾性,说掰断就得掰断,如果一开始掰不断,那么整个这一根你就休想掰断,真让人匪夷所思。我们掰芦稷时都很小心,否则,弄出声音,会让大人跑来抓住。第二天,被偷的那户人家并不急恼,他们知道是镇上的孩子偷的,就到镇上晃悠,说谁家的伢儿掰了芦稷的,请把穗头送来。我们又趁着月色,将穗头如数归还。我们知道,芦稷是扎扫帚的极好材料,远胜于稻穗或高粱穗,坚固而不失弹性,美观而又耐用。因此,秋后洁净坦荡的场院便是用它打扫成的。
不仅孩童将芦稷视为珍贵之物,即便青年男女也将之视作心爱之物。情窦盛开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披着月色出来幽会时,为了要摸到某个隐秘的树林,或流着水声又长满青竹的河边见面,便先用芦稷秆权作手杖探路,或驱逐跟踪的野狗。待到会面后,便一边娓娓叙着情话,一边嚼起芦稷。待芦稷吃完,便各自娴熟地用芦稷篾编成一块蒲席坐于一起去,共享夜之温柔。而有了女子的长者,尤看重芦稷。秋天,小镇一带的庄户人家女儿出嫁,为了恪守“出嫁路上不喝水”的乡规,又不让女儿委屈,母亲便将芦稷斩断后用红布包了,悄然塞给女儿;儿子要出门了,父亲会粗野地说一声“自个儿到田里砍芦稷去”。若有亲朋自远方来,定然先用芦稷招待一番,常有客人能一气吃十数根,然后美美地敲着鼓起的肚子,极快意地舒出一口气来,那一夜他肯定要酣睡到天明。那些年我下早潮海,一路上拔田边的芦稷,其时夜半更深,四周无人,只有月亮孤独地挂在天上,村舍的房屋如巨兽默然趴在那儿。我可以放心大胆拣最粗的熟透的芦稷拔,边走边享用,寂静中只听到我嚼芦稷的声音,一直吃到滩涂。小镇有个民间传说,有个孩子揣着馒头去远处玩耍,怕迷路家人找不到他,便掰馒头屑子扔在路上,这样家人就能凭馒头屑寻到他,可是馒头屑最终为鸟所食,那孩子终是没找到。而我根本不用担心,我吐了一路的芦稷渣子,没有哪只鸟肯吃,如果谁有兴趣,完全可以循着芦稷渣找到在滩涂上奋力取蛤的少年。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去东海部队看电影,会左手提溜着爬爬凳,右肩上扛着几根芦稷,边看着心仪的电影,边吃着芦稷,然后身边再坐着心仪的女孩,再没有比这个更幸福的了。
那么,耄耋之年呢?人们再也没有了芦稷那样火红色的热情了,他们静静地坐于芦稷荫里,回首过去了的欢乐和痛苦的岁月,他们也许有一种被芦稷离异了的惆怅,因为他们再不能用没牙的嘴去啃芦稷秆,再不能用芦稷叶做成叶笛,吹奏一段喜爱的曲子,甚至再不能用颤巍巍的手扎芦稷扫帚,去扫净赴黄泉的路。但忠厚的芦稷并没有忘记他们。我记得小镇上有个老奶奶八十岁那年,一块痰堵在嗓子眼快要憋过去,儿子便用榨出的芦稷汁喂她,须臾,老奶奶将痰咳了出来,且脸面有了红润的血色。正是靠了芦稷汁,老奶奶的生命之舟才渡过了她人生的第八十一条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