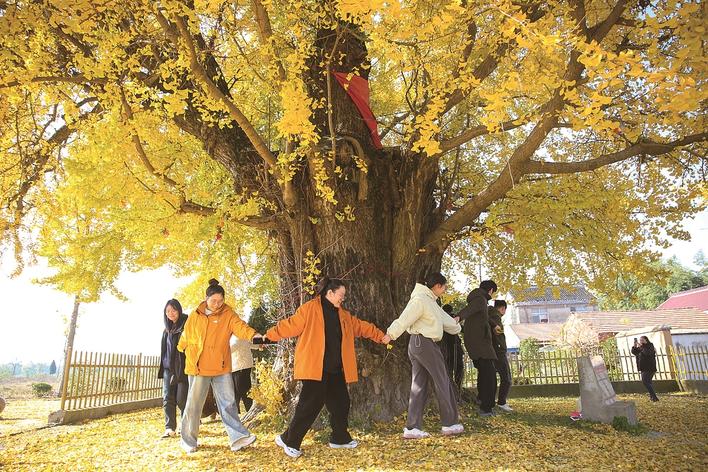□谢志军
凌晨,窗外的风一阵紧似一阵,“呼呼”声掺杂着雨的潮气,也像冬天匆忙赶来时发出的声声喘息。天,真要冷了。
我把被子往身子底下掖了掖,琢磨着是时候把那条厚被拿出来盖了。厚被十二斤重,长两米二、宽两米,原先为两条六斤重的被子,那是结婚时母亲为我准备的。那时的床没现在大、那时的被也没现在大,那时的人在寒冷的冬天大多盖两条被子。后来,妻子说:“你个高腿长,被子大点,盖在身上才舒服。”于是,她把这两条被子加工成现在的一条大厚被。我喜欢这条厚被,它留存着新婚的缠绵,也留存着母亲的心思。那丝丝缕缕,是母亲当年一朵棉花、一朵棉花精挑细选的。
原先那两条棉被,是祖母和母亲在一个晴朗冬日的午后,一针一线用心缝起来的。那天是个好日子,婆媳俩一边缝一边说着吉祥话:“新被上床,龙凤呈祥,早生贵子,金玉满堂。”
棉花是母亲种的,长在村子东南角的那块八分地里。那是一片淳朴厚实的土地。长棉花,不容易,其间吃过的苦、流过的汗,好比一位母亲将呱呱坠地的婴儿拉扯成人高马大的青年。
三月底四月初,乍暖还寒,一粒粒饱满的棉花种子住进圆柱形的营养钵,一个个营养钵又住进竹条搭建的大棚。白天,掀开大棚透透气;晚上,将大棚遮得严严实实。如同年轻的母亲夜间不时查看身边的婴儿,冒汗了,将被角掀一掀;蹬被了,将被子拉一拉。
育苗期间,母亲不仅关心棉花出苗,还要忙着平整一块土地——那是幼棉未来的家园。经历一个冬季的天寒地冻,碎土整地并不轻松,坚硬的钉耙磕着同样坚硬的泥土,需要的不仅是力气,还有巧劲:挥起、抡下、扒地,阳光下钉耙在空中形成一道道亮眼弧线,伴随着母亲的汗水与喘息。泥土碎到细无坷垃,开始筑垄。筑垄的过程又是细活:陇上的泥土需要上虚下实,垄与垄之间要抽出一条狭长的墒沟。垄筑成了,墒沟抽好了。一眼望去,道道棉垄像笔直的赛道,同样笔直的还有那条条墒沟。如果说,棉垄是棉花的宅基地,那墒沟,就是它赖以生存的河流,是棉花的生命之河。
谷雨要到了,大棚里的棉苗已长出三四片叶子,个子也有十几厘米高,到了棉苗移栽的时候。移苗期间,母亲非常忙碌,吃完早饭,带上午饭去棉田,天黑了才回家。先要在棉垄上挖洞,一个个纵横整齐、档距适中,母亲轻轻地捧着营养钵,一个个放进洞,幼棉也像鸟儿一样有了自己的窝。
五月阳光煦暖,催促着万物生长,棉花也在这灿烂季节迎来了天真烂漫的童年。大自然似乎特别眷顾这幼小的生命,晴好天气让它生活得惬意舒适。母亲却不闲着,除草、施肥、治虫,本不轻松的劳作,还被局限在小小空间,更需要加倍小心。如果哪一天不小心碰折了一棵幼棉,我能从母亲晚饭时的言语,感觉到一种轻微的疼。
转眼六七月到了,天气开始变得不听话,先是梅雨绵绵,而后常有倾盆大雨。遇上夜间大雨,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时,勤劳的人们会早早出现在棉田。他们或挖开墒口排水,或清理墒沟杂物,或小心翼翼地扶直倒下的棉枝;如果靠近一点,也许还会听见他们轻轻叹息。但是,这叹息好似夏天的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因为夏日的棉田到处散发着勃勃生机。且让我宕开一笔,先放下眼前如少年般疯长的棉花,去看看与它生长在同一土地的生命。这时,匍匐在这块地的,可能有青黑色的香瓜、肉白色的菜瓜、圆滚滚的西瓜……田头田脚,可能还有竖起的五颜六色的花架:豇豆花、黄瓜花、丝瓜花……迎风摇曳,多姿多彩。母亲总会把点滴土地侍弄好,从不让哪里空着,这也是那代人对待土地的珍惜与恭敬。
秋天来了,棉花也到了收获季节。每年这个时候,我喜欢到棉田里走走,那里有自然与人合作的美丽图画:朵朵棉花绽放枝头,洁白如玉、轻盈婀娜,风吹过时,如一朵白云亲吻另一朵白云、一张笑脸靠近另一张笑脸。是的,笑脸,丰收的季节,遇见的不都是忙碌的笑脸吗?这时候,只要晴天,棉田里总能见到女人摘棉花的身影,她们大多微笑着,手指娴熟地从这个枝头到那个枝头,仿佛在弹奏那首叫《丰收歌》的曲子。当然,这时候,如果碰上连绵阴雨,她们的脸也会阴着,那些烂掉的棉花果,那些即便没烂掉开出来的花也呈暗黄色的棉花果,折磨着母亲和乡亲们,那是一种庄稼人的痛。
摘下棉花,摊在芦苇席上晒干,装进干净的蛇皮袋,接下来要去卖了。棉花收购站在王庄桥口,离家四五里地。卖棉花,母亲很少单独行动,同去的往往还有几个一样能说会道的妇女。那个年代,卖棉花、交公粮都要面对收购员挑剔的眼光。棉花有等级、干湿之分,卖棉花需要几分机智,有时甚至“斗智斗勇”。我一直认为,庄稼人的淳朴与狡黠、委屈与无奈,卖棉花时表现得最为充分。我把这些时代的印记,连同朵朵棉花,存放在心中隐蔽的角落。
我已记不清,母亲最后一次种棉花是哪年,估摸着已过去了近三十年吧。但在今晨,听窗外秋风秋雨,朵朵棉花又在我心头绽放。前不久,母亲说:“老家还有两条留下的棉花胎,新的,没用过,留给孙子结婚。”我听罢不免感叹:母亲真是情意“棉棉”、瓜瓞“棉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