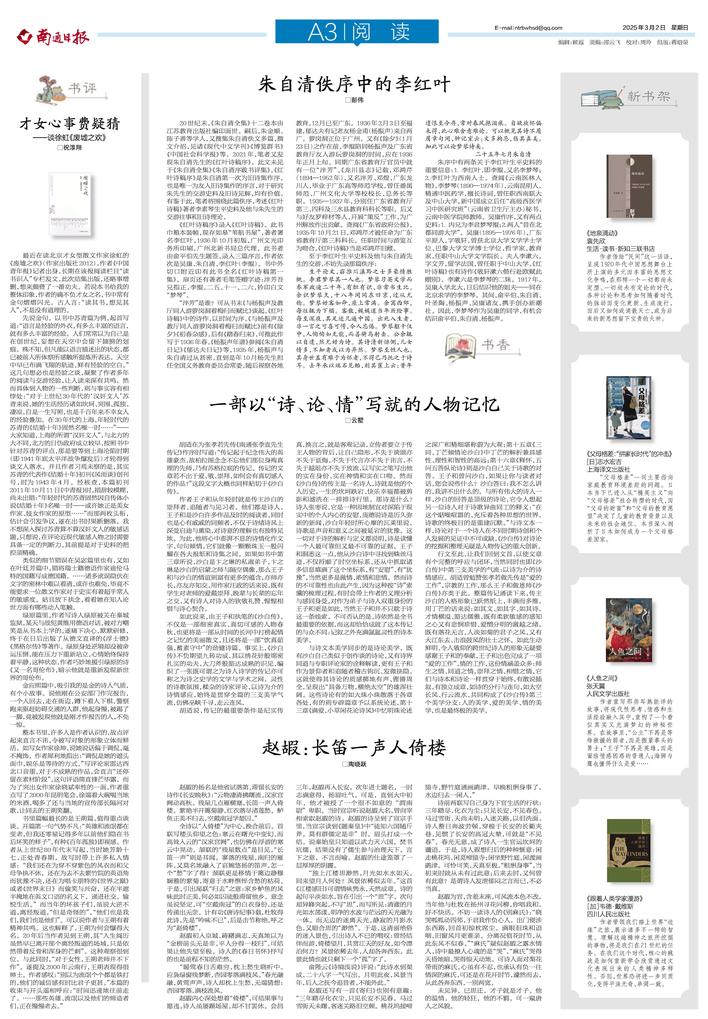□陶晓跃
赵嘏的扬名是他省试落第,滞留长安的诗作《长安晚秋》:“云物凄清拂曙流,汉家宫阙动高秋。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鲈鱼正美不归去,空戴南冠学楚囚。”
全诗以“人倚楼”为中心,挽合前后。首联写楼头仰望之色:寒云在曙光中变幻,而高耸入云的“汉家宫阙”,也仿佛在浮游的寒云中晃动。颔联的“残星数点”是目见,“长笛一声”则是耳闻。寥落的残星,南归的雁阵,又莫名地融入了哀婉悠扬的笛声,怎一个“愁”字了得?颈联更是移情于篱边静穆娴雅的紫菊,寄意于水畔憔悴含愁的枯荷。于是,引出尾联“归去”之意:家乡鲈鱼的风味此时正美,何必如囚徒般滞留他乡。意念虽说坚定,可“空戴南冠”的白衣身份,还是传递出无奈。计有功《唐诗纪事》载,杜牧得此诗,先是“吟味不已”,后是击节称绝,呼之为“赵倚楼”。
赵嘏初入京城,踌躇满志,天真地以为“金榜前头无是非,平人分得一枝归”,可结果让他失望至极。诗人的《春日书怀》抒写的也是前程不知的茫然。
“暖莺春日舌难穷,枕上愁生晓听中。应袅绿窗残梦断,杏园零落满枝风。”春光融融,黄莺声声,诗人却枕上生愁,无端猜想:杏园零落,满枝流风。
赵嘏内心深处想着“倚楼”,可结果事与愿违,诗人虽屡踬场屋,却不甘罢休。会昌三年,赵嘏再入长安,次年进士题名,一时志满意得,扬眉吐气。可是,直到大中初年,他才被授了一个很不如意的“渭南尉”卑职。当时宣宗听说赵嘏大名,曾向宰相索取赵嘏的诗。赵嘏的诗呈到了宣宗手里,当宣宗读到《题秦皇》中“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时,眉头打成一个结。说秦始皇只知道以武力灭六国,焚书坑儒,结果没有了儒生参与治理天下。言下之意,不言而喻。赵嘏的仕途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这首《江楼感旧》可谓情味隽永,天然成章。诗的起句平淡如水,旨在引出一个“思”字。次句却异峰突起,不写“思”,而写所见:清澈的月光如水荡漾,明净的水波与茫远的天光融为一体。而无边的迷离天光,静寂的月影水色,又暗合思的“渺然”。于是,这清丽绝俗的迷人景色,引出诗人不已的喟叹:曾经结伴而游,倚楼望月,共赏江天的好友,如今漂泊何方?风景依稀去年,人却各奔西东。此景此情也就只剩下一个“孤”字了。
俞陛云《诗境浅说》评说:“此诗水到渠成,二十八字一气写出。月明此夜,风景当年,后人之抚今追昔者,不能外此。”
赵嘏还写有一首《寄归》也别有意趣:“三年踏尽化衣尘,只见长安不见春。马过雪街天未曙,客迷关路泪空频。桃花坞接啼猿寺,野竹庭通画鹢津。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
诗前两联写自己身为下官生活的行状:三年踏尽,化衣为尘;只见长安,不见春色。马过雪街,天尚未明;人迷关路,以泪洗面。诗人整日奔波劳顿,穿梭于长安的长衢夹巷,见惯了长安的高冠大辇,可就是“不见春”。春光无意,成了诗人一生官运坎坷的谶语。于是,诗人遐想归后的种种惬意:闲走桃花坞,闲觅啼猿寺;闲坐野竹庭,闲渡画鹢津。可怜可笑,天真至极。“粗酬身事”,当初来时就从未有过此意;后来去时,又何曾有此意?是谓诗人发泄郁闷之言而已,不必当真。
赵嘏为官,含羞末座,可风流本色不改,当年他与杜牧在扬州寻花问柳,你唱我和,好不快活。不妨一读诗人的《别麻氏》:“晓哭呱呱动四邻,于君我作负心人。出门便涉东西路,回首初惊枕席尘。满眼泪珠和语咽,旧窗风月更谁亲。分离况值花时节,从此东风不似春。”“麻氏”疑似赵嘏之露水情人,诗中最撩人心魂的是“哭”,“麻氏”哭得天昏地暗,哭得惊天动地。可诗人面对梨花带雨的麻氏,心虽有不忍,也承认有负一往情深的麻氏,可还是在花开时节,遽然而去,从此各奔东西,一别两宽。
未见异,已思迁,才子就是才子。他的滥情,他的轻狂,他的不羁,可一窥唐人之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