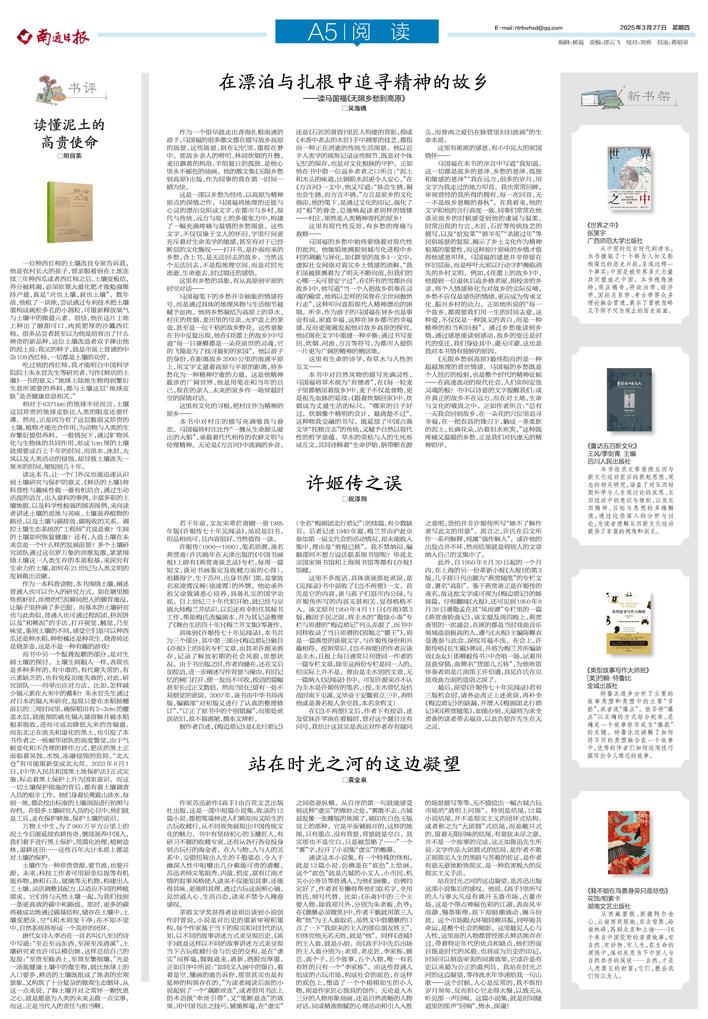□袁金泉
作家苏迅新作《高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的12篇小说,都把笔端伸进人们熟知而又陌生的古玩收藏行,从不同视角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书中有坚持初心的玉雕匠人,有研习不辍的收藏专家,还有从各行各业投身到古玩行的淘金者。在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中,交错扭转出人生的千般姿态,令人于幽深人性中咀嚼出几分难能可贵的清醒。苏迅老师文笔娟秀、内敛、俏皮,富有江南才情的叙事风格使人读来不仅能知其事,还能得其味,更能明其理,透过古玩这面照心镜,见世道人心、生活百态,读来不禁令人掩卷感叹。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谈到小说创作时曾说,小说是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重构,每个作家基于当下的现实和对时代的认知,以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来呈现历史。《高手》就是这样以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来呈现当下古玩收藏行业与历史的交构,是在“虚实”间挥毫,娓娓道来,清新、洒脱而厚重。正如自序中所说:“如同文人画中的留白,看着是空,懂画的能告诉你,那里其实也是有延伸的构图存在的。”为读者阅读后面的小说起到了一个“藕断丝连”,或者借用书法上的术语既“牵丝引带”,又“笔断意连”的效果,用中国书法之技巧,铺墨挥毫,在“虚实”之间恣意纵横。从自序的第一句就能感受到这种“虚实”的微妙之处。“雾散不去,古城益发像一张雕版的地图了,刷印在白色玉版宣上的那种。它是平面铺展开的,这样的地图,只有重点,没有背景,背景就是空白。其实那也不是空白,只是被忽略了……”一个“雾”字,拉开了小说集“虚实”的帷幕。
通读这本小说集,有一个特殊的怪相,就是12篇小说,仿佛是在“底色”上绘画。这个“底色”就是古城的小文人、小市民、机关小公务员等普通人,为他们画像。仿佛约定好了,作者甚至懒得帮他们取名字,全用姓氏、绰号代替。比如:《乐斋》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除我郑月外,分别为朱老板、仇爷;在《貔貅必须微笑》中,作者干脆就用第三人称“他”为主人翁取名,虽然文中借貔貅的口点了一下“我原来的主人的那位朋友姓王”,但终究他无名无姓,就是“他”。同样《进城》的主人翁,就是小胡。而《高手》中先后出场的主人翁分别为:老郑、老皮匠、李家栋、顾总、高个子,五个故事,五个人物,唯一有名有姓的只有一个“李家栋”。由这些普通人组成的古玩市场,构成社会的底色,在这样的底色上,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人物,则是作家匠心独具的创作。无论是入木三分的人物形象刻画,还是自然流畅的人物对话,间或精准细腻的心理活动和引人入胜的场景描写等等,无不描绘出一幅古城古玩市场的“清明上河图”。特别是结尾,12篇小说结尾,并不是现实主义的闭环式结构,或者称之为“大团圆”式结尾,而是敞开式的,留着无限回味的结尾,有意犹未尽之意,并不是一个故事的完成,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文学作品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作者不敢正视现实人生的黑暗与苦难的佐证,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粉饰现实,是一种危害极大的反现实主义手法。
站在时光之河的这边凝望,是苏迅出版这部小说集后的感叹。他说,《高手》里所写的人与事大凡没有离开玉器市场、古董市场,这是个带点神秘色彩的江湖,表面风平浪静、慢条斯理,底下却暗潮涌动、缠斗纷扰。这个市场跟大环境同频共振,同呼吸共命运,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这里最见人心与人性,这里面的人物都曾经那么鲜活地存在过,带着特定年代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面目既是时代的风貌,也将成为历史的印记。时间可以制造审美的间离效果,它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为公正的裁判员。我站在时光之河的这边凝望,等待流水年华递给我一句山歌——这个时候,人心是反常的,我不惧怕岁月匆匆,反而担心它走得太慢,以致无从听见那一声回响。这篇小说集,就是时间隧道里的那声“回响”,隽永、深邃!